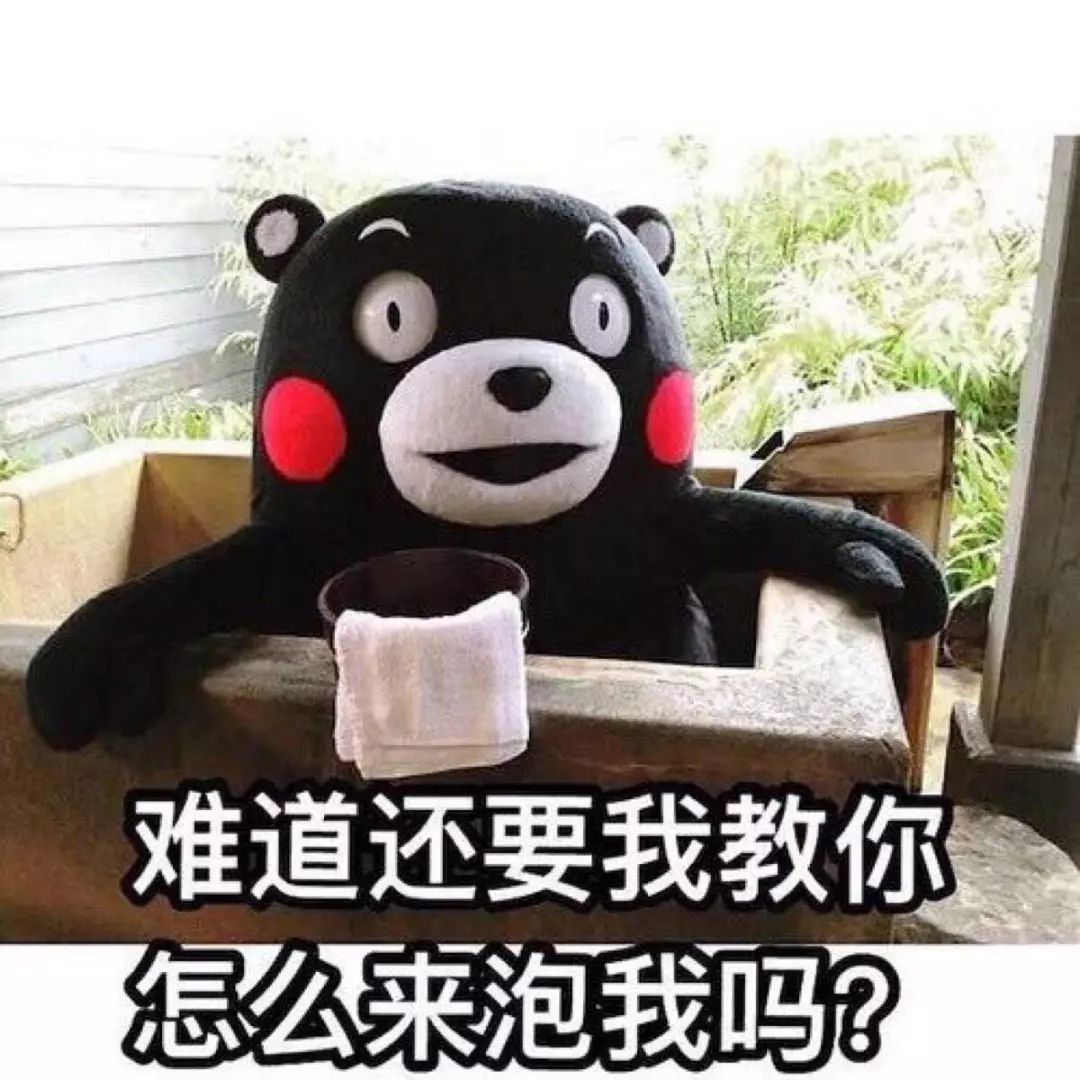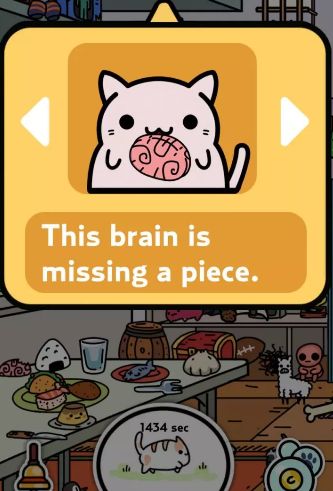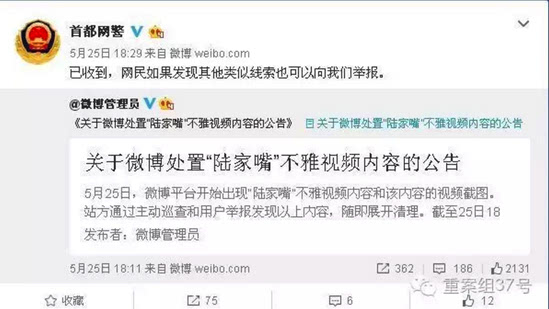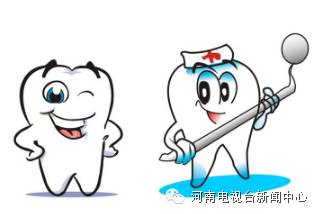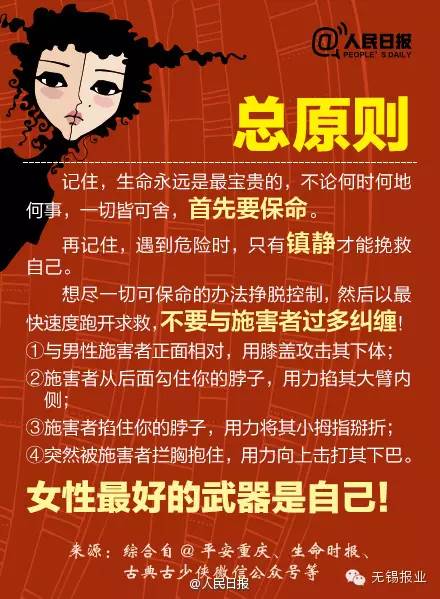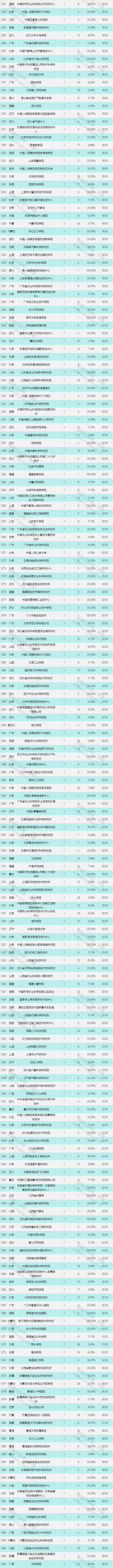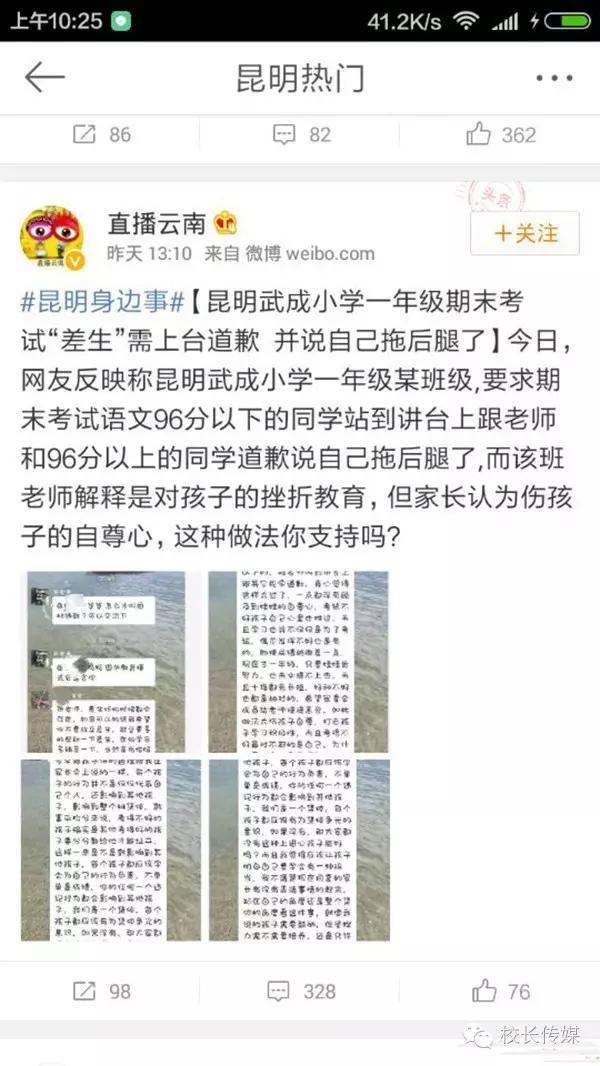1989年的三月上旬、(三十年前)正好利用出差湖南长沙的机会重返红土地——江西省铜鼓县、去看望我朝思暮想的老表们、离开他们一晃间竟十五年过去了。
班车在大山深处上坡下坡、崎岖蜿蜒的土路上艰难地前行、苍翠欲滴的群山在迷茫的晨雾之中若影若现、空气清新令人陶醉、不知疲倦的小鳥争相鸣叫、并大胆地略过车窗、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犹如吹奏着萨克斯、不断的变换着音符、上演了一曲曲动人的旋律、撩拨着我那个十分愉悦的心情。思绪把我带到了二十年前…
那 一张张笑脸和蔼可亲的面孔不断的清晰涌现,最后定格在“模迪婶”身上,尽管他老人家去世已近十年、但是她的一笑一颦、和霭可亲的模样却是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74年告别她老人家后、没想到从此就阴阳两隔、相会无期、令人扼腕痛惜、唏嘘不已!(据说模迪婶姓朱、但大家都叫她模迪婶、所以她的真名也就慢慢地被遗忘了。金生的父亲是胡模迪、系“迪”字辈的、记得胡姓家族的辈份是从“西、东、则、贤、人、迪、尔、业、维、琴”起、分为十代,后不详之。69年有幸见到胡姓家族中高辈份老人—付贤公、并有幸同他老人家一起生产劳动、聆听了他的幽默见解、见证了他的诙谐搞笑、并在高水洞教授于我如何做笋干、共度了一段山里的美好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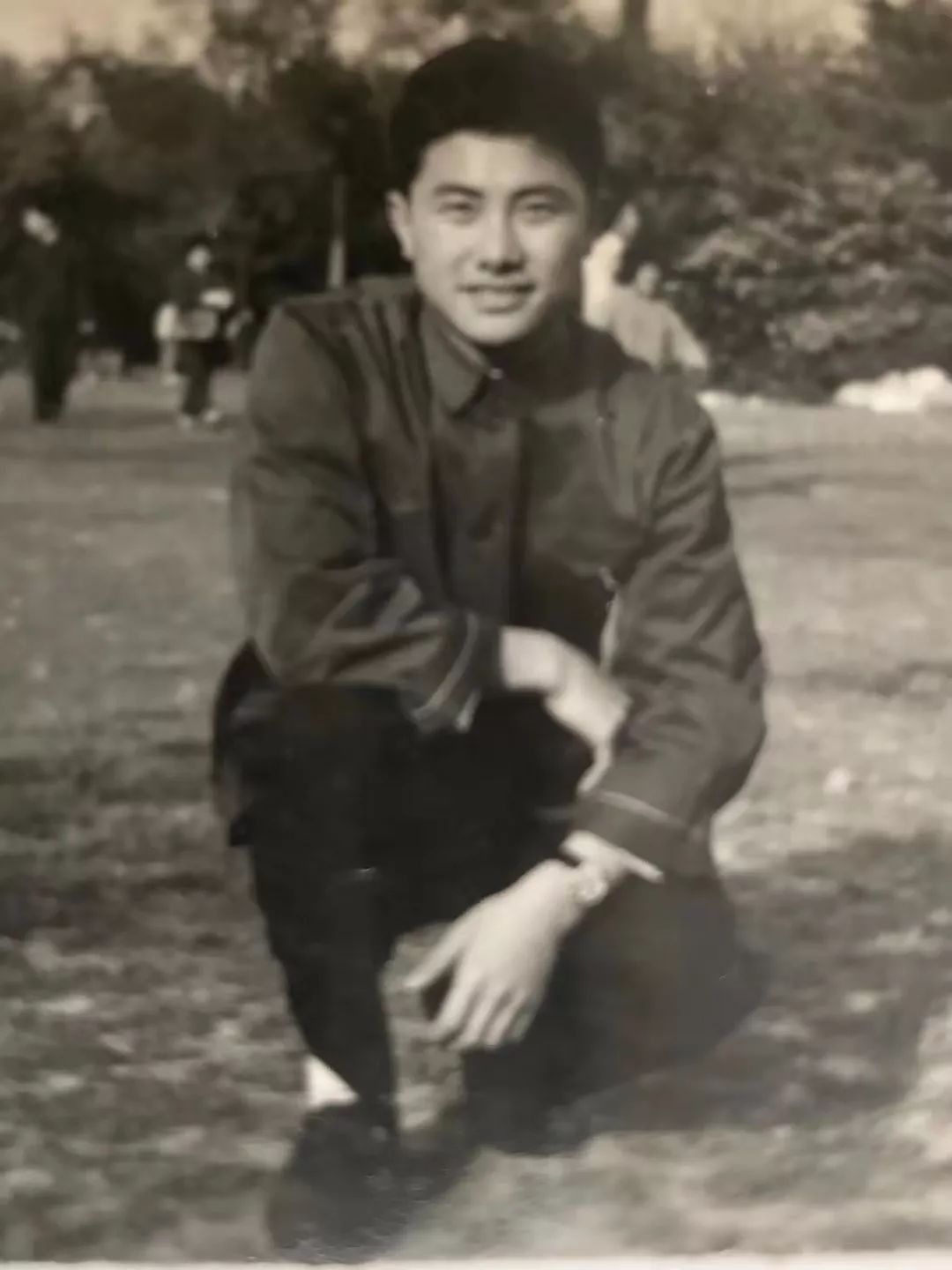
(图为 1974年曹小伟离开铜鼓调回上海留影)
一、初识模迪婶
69年3月23日我们坐火车离开上海、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铜鼓县带溪公社驻地席地而坐一宿后、于25上午大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在“咚咚咣、咚咚咣”单调乏味的锣鼓声的引导下、来到了山清水秀、四面环山、景色宜人的东源大队、被分配到清洞(三队)的八位同学3男5女都是来自一个中学的同学。我们被带到一座破旧的房子里面、放下行李就“参观”起这座老宅、后来听说这是一户地主家的房子、八个同学无不深感诧异、这是地主家住的地方吗?简陋不算、简直破败不堪,当时我们对地主、富农都十分的痛恨、因为教科书上说他们是“剝削阶级”、欺压农民的,但鸠占鵲巢的事情也不见得那么地“光明磊落”、我想这个地主也够“可怜”的了、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被“扫地出门”了!唉……
有两位老人正在忙碌着、在桌上为我们泡茶、只见一位瘦瘦小小干干净净,穿着一身青布衣服的老太太、给我端来了一碗茶、我赶紧双手接过了茶碗连连感谢、再一看、哈哈!那碗茶也太有特色了、有好多五颜六色吃的东西搁在里面、喝完了带着淡淡咸味的茶水、便将泡在茶中的东西留在碗中、这时这位老太太十分亲切地用浓重江西当地囗音的“普通话”对我说“这是果子”、“很好吃的”、“把它们都吃掉、不吃就浪费可惜了。”然后就告诉我这碗茶叫“果子茶”、是这里老表们招待亲戚朋友必不可少的一种礼仪、而茶碗中的“果子”的品种和多少、则可以看出主人家的富有和待客的程度,这“果子”一般是由茶叶、菊花、香椿芽、芝麻、花生、黄豆子、冬豆子、胡萝卜干、白萝卜干、勺瓜干、豆角干等、就是通过腌制能久藏的果蔬类干物组成。后来慢慢地了解知道了、江西老表都特别的好客、他们生活在一起十分和睦、无论是熟人还是从不相识的陌生人经过这户人家、或在家门口小憇、主人总会端出一碗果子茶请你、而且无论十个、八个熟与不熟都一视同仁。(城市里的邻居们多的是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点上来说城乡差别却是蛮大的!(许多地方农村的文明程度高于城市)
后来别人告诉我她是“模迪婶”、噢!原来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叫模迪婶、住在我们后面的房子里、中间相隔着一个小菜园子。

(图为 1969年在东源修河堤时东源大队的部分知青)
二、两片“神奇” 的小药丸
五六月份的一个晚上,正在熟睡中的我,忽然听到一阵阵痛苦的哭声、哭声让人感到心慌不安、不能入眠。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去后面问何故?原来模迪婶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已嫁到奉乡(这里人们称九江市修水县的上奉公社为奉乡)大儿子叫金生、小儿子就是伢俚!昨晚的痛哭声是由于模迪婶的大女儿因病不治而亡故了、在这生离死别中、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黄梅不落青梅落怎不叫人痛彻心肺?想去安慰一下、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确是件人间悲剧、难怪模迪婶哭得死去活来了。
连续几天的哭泣早已心力交瘁、气息奄奄。过了一段日子又听到后面不时传来十分痛苦的干嚎声、于是急忙又过去问究竟?原来经过许多天的极度疲惫和悲伤、精神和身体都呈现十分虚弱的状况、可能是诱发出生理上的其它疾病、模迪婶捧着胸口痛苦不堪、脸都变了色。据说都两天没吃东西了、我急忙问金生“何不送医”?金生回答“已请阁郎中”、可郎中问诊后、日:“冒药、打不当阁”、就走了,也不知道是这个郎中学医不精?还是确实没有有效的药物?但我猜想应是后者居多,否则怎么叫做“穷乡僻壤”呢?所以物质奇缺!难道让模迪婶一直这样地受痛苦? 彷徨犹豫中、“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鼓起勇气详细地询问了模迪婶的病情、头脑中飞速思忖各种病症、于是乎对金生言道、这可能是由胃病所引起的胃痛、我有药、你敢不敢给她吃?(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也敢胆大妄为?竟敢下药?也难怪五十年前的人、是那么的纯朴可爱的、总是基于出发点,那像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心怀叵测?不碰瓷才怪!)见他点头同意后、(金生也是病急乱投医)我立马取来了“普鲁苯辛”、安排她服下此两粒小小的药丸、不消半个时辰、模迪婶脸色平和、呼吸均匀…好了?不痛了?真的好了!奇了怪了、我都能成为医师了?心中狂喜差点儿没得意忘形、但还是装出一副很老成的样子、连连点头说“意料之中、意料之中”,其实来江西务农前、我曾恶补医疗卫生知识、因此稍稍地了解一些常见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生怕自己得了病而两眼一抹黑再遇上庸医怎办?多少自己都要懂一点就行、真的不痛了?倾刻间我也为自己的果断而自豪。以后模迪婶见人就说“曹家人晓得计敖啊、还会打病角”。但这件小事确实大大地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感,康复后的模迪婶还专门做好吃的犒劳我。

(图为 曹小伟与胡金迪全家在东源合影留念,拍摄于2018年春节)
三、阻绕放棑
那时年青不知天高地厚、忽突发奇想要去队里参加放棑、(不过也是很难办的、因为放棑的大师傅们都生产队里的骨干、最敖的、怎敢和他们比肩?)不过还是应该先去了解如何放法、水流湍急高低不平、大小石块布满河床、高低桥板转弯抹角随处可见,必须从理论上学起增加感性知识。于是从二方阁经火堂、落义堂、上司马第到牌坊下、请教了多位高手才基本掌握了放棑的基础理论知识(当然只是纸上谈兵)就差实践了、其实这也就如学游泳、在岸上讲得口若悬河、青筋凸起、唾沫横飞、滔滔不绝、还不如下水去卟咙卟咙几下、效果好得多了。在这里应该感谢多位博学多才的老表、因为他们无私地传授了经验和教训、帮我迅速掌握放棑技巧、成为尔浩队长帐下的又一名战将这是后话。司马第尓锦还借我一支上好的竹镐、帮我完成心愿。现在做通了尔浩队长的工作、又借来了犹如“唐吉柯德”手中的那杆长枪的竹镐跃跃欲试、可在这紧要的档口,模迪婶来了、坚决反对我去放棑,“不许去!”并把曾经出过的事故一一搬出来“恐吓”我、美其名曰“太过危险”!说是要对我上海的父母负责,这时我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真学来的如何放棑的心得告诉她、如何驾驭竹棑过桥、桥分高高低低各不相同、因此如何避让、身手也是进退有序见招拆招、并非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什么是危险地段、如何避让危险、想方设法地让她放心、但她始终都不相信我那些学来的“经验”、但也听得她瞠目结舌、却是无法反驳、因为面对的俨然是一个放棑的“高手”…
那天早上、我兴冲冲地肩着竹镐去上面的“肖水坑”准备开工放棑、只见模迪婶竟然也赶了过来、她是想在最后关头能成功地劝阻我、因为从她的双眼中我看到了她的万分关切的神情、肖水坑这边已是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尔浩队长正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全部劳动力、肩树枝的、整理竹子的、扎萝杷的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一只只竹棑下水了、终于轮到我了、在大都老表的惊奇、震惊、疑惑、称赞、肯定的瞩目下、我同模迪婶招了招手算是打了招呼、便义无反顾、兴高采烈地就登上了竹棑、她见到我雄赳赳气昂昂如天神般地䇄立在竹棑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下、伴着轰轰隆隆的竹棑和河水中大石块的巨大撞击声中、双手紧握竹镐威风凛凛地样子、全神贯注搖摇晃晃地驾驭着竹棑施施然地向下游进发、终于放心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也引来了全部的赞许的目光。这天我一共放了五个萝杷、放下去的时候那叫一个“爽”字难得、可是从柳溪大队那边走回来到是有点路远。收工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模迪婶那儿“汇报心得”、我绘声绘色地把放棑时看到的景色一一告诉她、自己如何小心地避开“灵兴端”(可能是“灵兴潭”)、她见我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兴口开河地讲述着,不由地露出了欢欣的笑容、但第二天一早她还是跟在我后面叫喊着“好省来、好省来!”(意思就是当心点!当心点!她还是有点不放心。)以后她总是对别人说“毛想到、上海的知青曹家人都有阁敖!棑都会放?!希里事都会制”。(在生产队中真正能下河清洞放棑的老表也是不多的、胆小怕危险的居多)。

(图为 曹小伟在铜鼓东浒大樟树前留影 拍摄于2018年春节)
对曹小伟来说,模迪婶不仅是房东,更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在铜鼓的那段时光虽然艰苦,但也是一种成长,铜鼓老表对知青们的浓浓情谊更让他们终生难忘!曹小伟退休后每年都会来铜鼓过年,所以写下这篇文章纪念模迪婶,回忆当初在带溪插队的峥嵘岁月。 因全文篇幅太长,所以分为两部分推送,欲知后事如何,请关注乐在铜鼓!
作者:原带溪公社东源大队三队(清洞) 上海知青 曹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