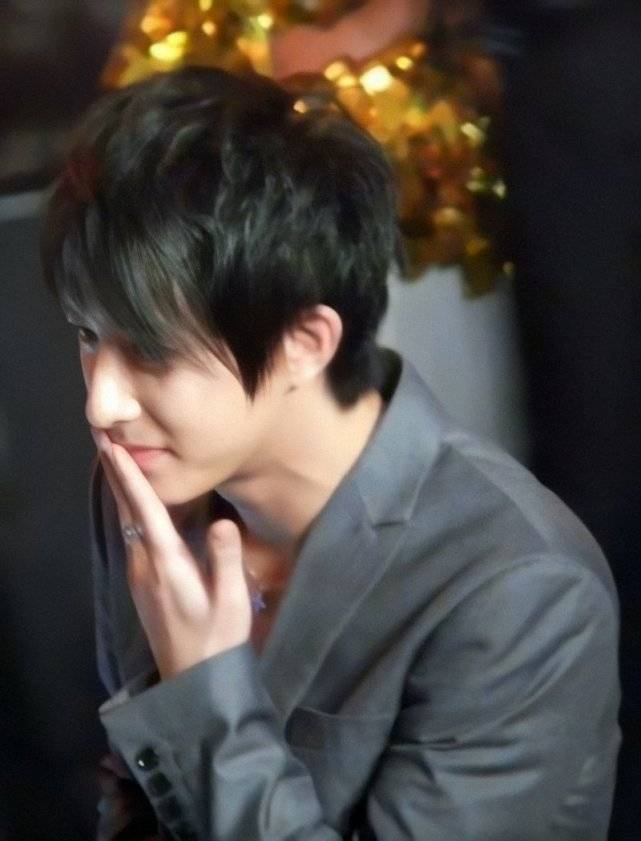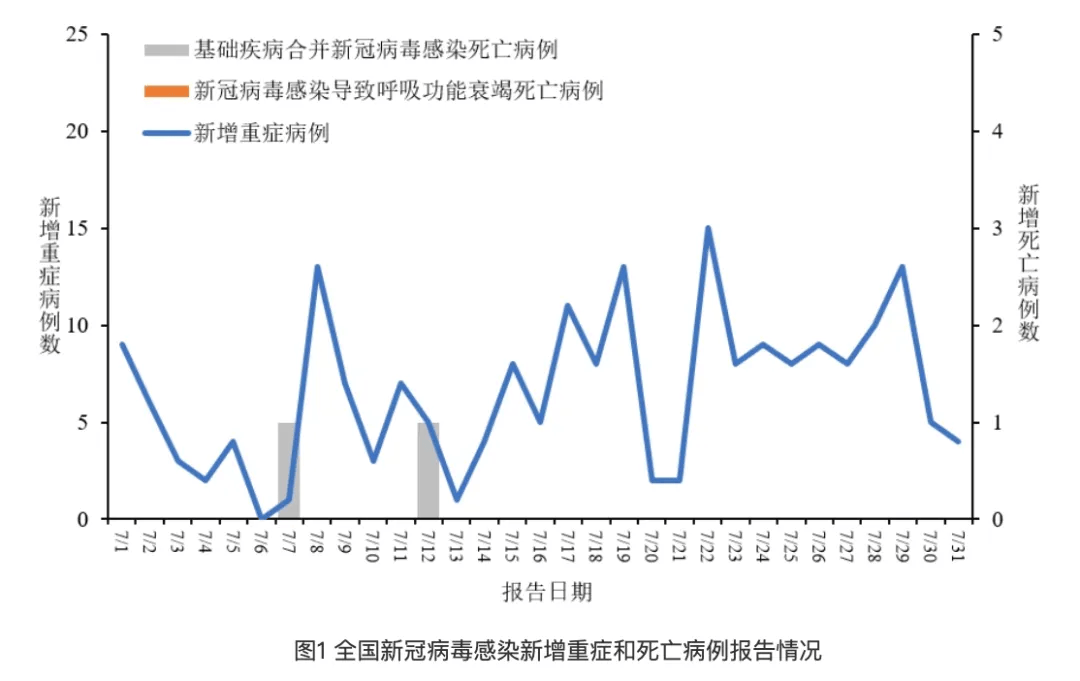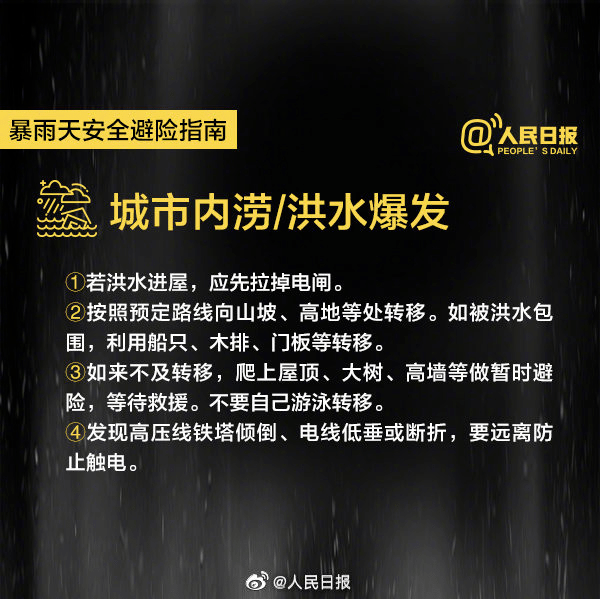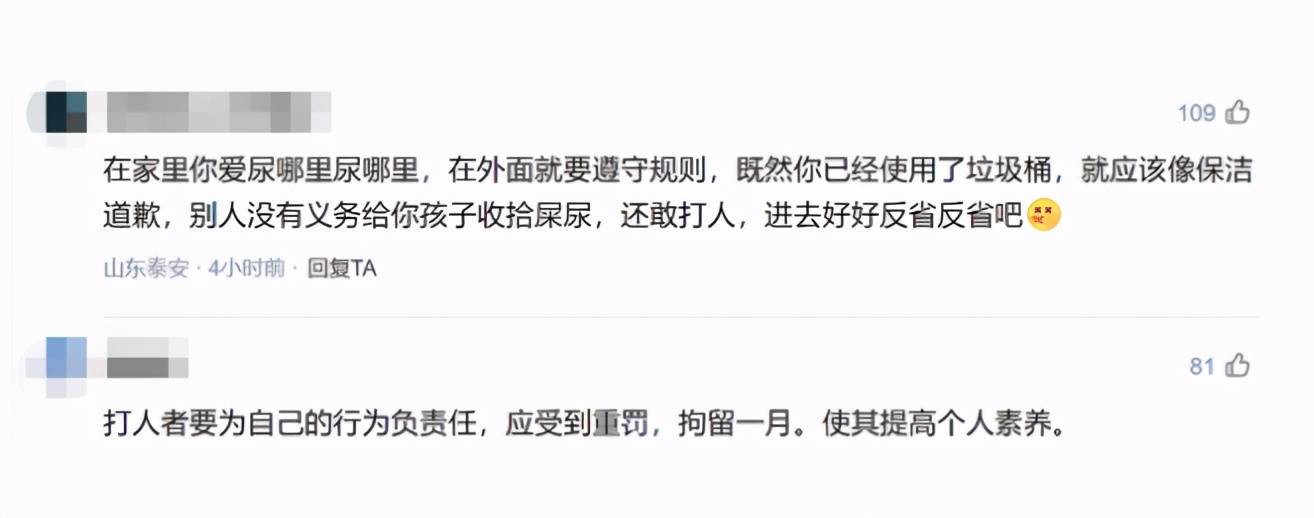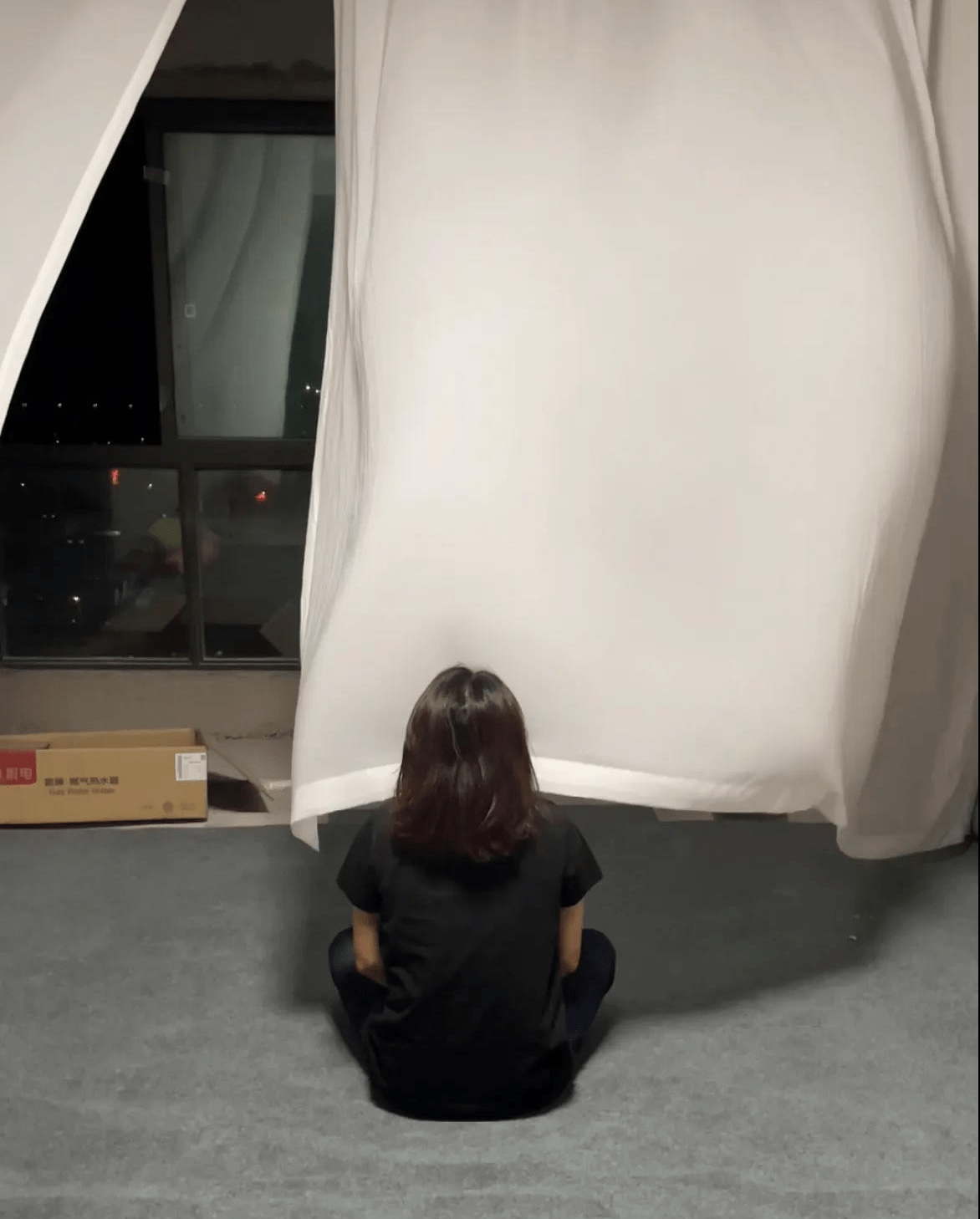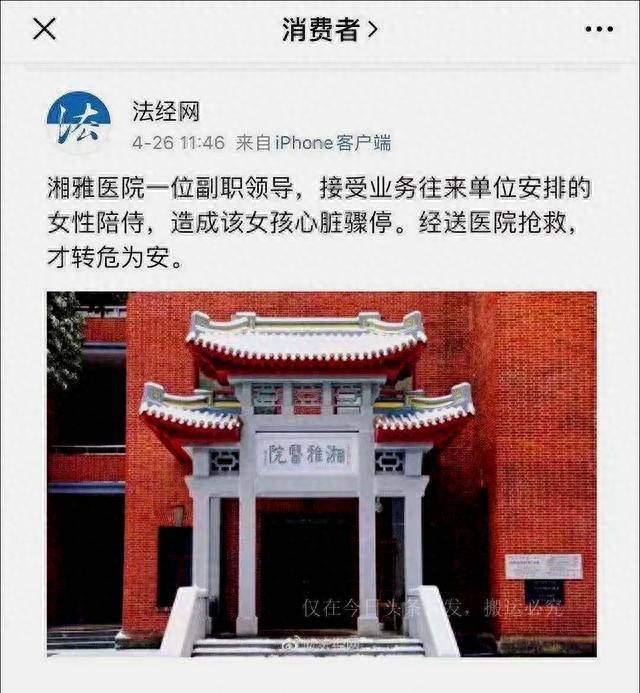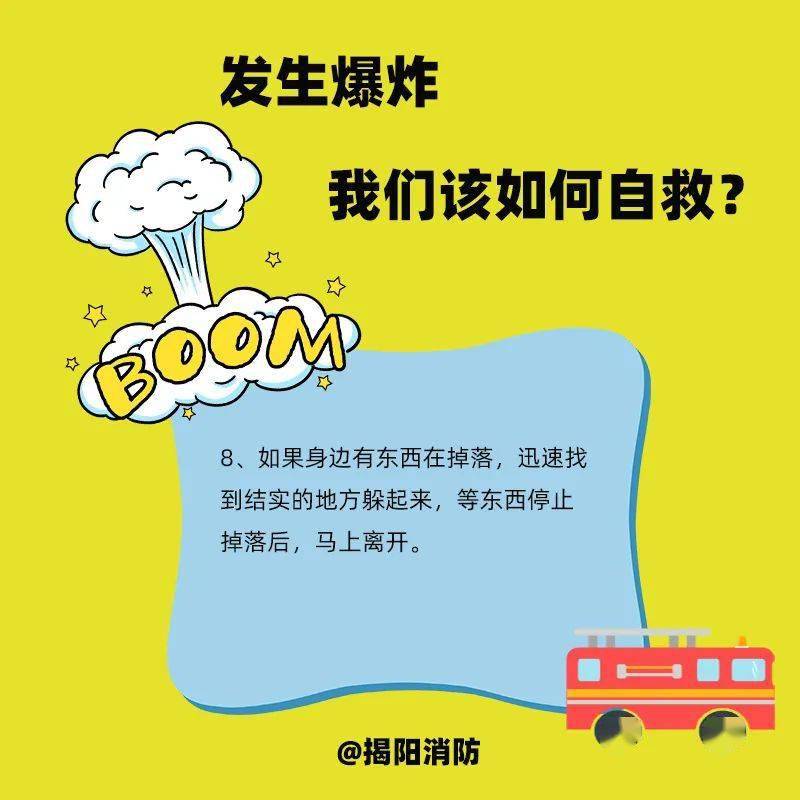当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呼唤教育创新,并且开始在学校中进行课程设置、教学技术和学校治理方面的试验。但是,有没有可能建立一所真正的进化型青色学校(文末附青色组织介绍),那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德国柏林市中心的ESBZ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

ESBZ 打开了教育的另一扇门
ESBZ 打开了教育的另一扇门
ESBZ是一所创办于2007年的7~12年级中学,该校从获得批准到开门招生的过程显得相当匆忙。离学年开始仅有3个月的时候,市议会突然决定把一座老旧的预制板楼房交给一群不肯放弃梦想的“烦人”家长。学年开始时,只有16名学生注册,几个月之后,到了年中,又有30名学生加入,大部分是其他学校拒收的学生或者开除的“问题”学生。对于这样一所学校而言,很难说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但仅仅几年的时间,这所学校发展到了500名学生的规模,并且吸引了全国数百名校长、老师和教育专家前来参观学习。
这所学校的精神支柱就是家长们从德国西部招聘来的校长玛格丽特•拉斯菲尔德(MargretRasfeld)——一位激进的革新者和曾经的科学老师。2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深刻改变了拉斯菲尔德对孩子和教育的理念,也播下了这所学校的种子。 1986年,她教的几个八年级学生找她讨论学
校发生的暴力、欺凌和敲诈勒索的问题。她说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到她家谈谈,那里说话更方便。第一次来了16名学生,一周后来了33名。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希望从她那里获得答案,她也没有答案,但她帮助他们走上了探索的旅程,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她从孩子们身上发现了她以前从未看到的一面,她为孩子们从他们自己身上发现的勇气、坚持、韧性、才智和同情心而惊叹,而这些品质从未能在学校里被激发出来。从那时起她就坚信,教育应该激发孩子们真正的潜力和真实的本性;她希望不仅能激发他们的思维,还要吸引他们投入双手、内心和灵魂。
如果你去参观ESBZ,在校门外就能感觉到这所学校有些特别,这种感觉来自孩子们的状态,他们走路的姿势和互动的方式。学生们不是在大门附近晃悠,到了最后一分钟才磨磨蹭蹭进教室;相反,他们是兴高采烈地直接迈向教室的。他们的神态中透出沉静的决心与专注,他们的心思已然投入到某个项目之中。这里并没有青春期的故作姿态和各种比“酷”。
学校在创立原则中就申明,所有的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都有各自的才能可以贡献,他们都是宝贵的、值得珍视的和被需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孩子们迈进学校的样子就在告诉我们,这些原则不仅仅是纸上的文字,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姿势和神态直接体现出这些原则的精髓。
学生自主学习 + 互相学习
学生自主学习 + 互相学习
ESBZ是如何执行这些原则的呢?首先,孩子们得为他们的学习负全责,在很大程度上,学生自学并且互相学习;成年人承担导师和教练的角色,只是在必要时担任传统的教师角色。他们给予鼓励、建议、赞扬、反馈和挑战,学习的责任牢牢掌握在学生手里。
这种自主学习是先从几门主课开始的,包括语言、数学和科学。
学校首先取消了这几门课的正式讲授,老师把这些科目划分成不同的模块,再把每个模块的理论、练习和测试印在大号抽认卡上,然后由学生自己决定学习的进度。
数学有困难的学生可以在数学上多花时间,而在觉得容易的科目上少用时间。各个模块都设有高阶内容供有兴趣的学生选择,但不是必修。学生可以自学,也可以根据需要组成学习小组。他们有问题时会先问同学,只有在同伴们帮不上忙的时候才会去问老师(老师因此能够腾出时间来做深度的个别辅导)。
班级都是混龄的,七、八、九年级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孩子们在学习者和教师的角色之间不停切换,大孩子也能从帮助小孩子的过程中学习(复习以前学习过的内容)。因为学习进度可由学生自己掌握,所以ESBZ非常包容。每个班都有几个患有自闭症和有不同程度学习障碍的孩子,要在以往其他学校,通常他们会被降级并送到特殊需求学校,但在这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与其他同学一起学习。

在这里,学生的社会背景格外多样化:20% 来自少数族裔家庭,25%有资格领食品资助,而大约25%来自社会阶层的另一端,其家庭背景非常优越。
一对一导师交流 + 学习内容自由选择
一对一导师交流 + 学习内容自由选择
每一名学生都有一个笔记本,用来记录他们的学习成果。学校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对每一名学生的年终成绩都有明确的期望(学生们如果对某个科目很有激情,那当然可以超出期望值,很多孩子都会这样选择)。每周五,所有孩子都会跟自己的导师进行一对一谈话。他们一起讨论本周的进步、遇到的问题和下一周的计划,以及萦绕心间的情感或关系。
通过这些一对一谈话,老师和同学得以互相深入了解,师生之间的联结比传统学校要深厚得多。孩子们知道:有一个人真的在乎我,有一个人愿意听我说话。一年两次,学生在与导师的谈话中确立半年的三个目标。例如,有个叫保罗的13岁害羞男孩,他设立的一个目标是更放松地让别人看到自己,他想学习的一件事就是更多地当众发言。
基本科目的自学时间是早晨的前两个小时。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则用于贴近实际生活的个人或集体项目。有些学生重新设计学校建筑的一部分,然后协调翻修工作;其他人可能会努力让市议会采纳更高的环境保护标准。学生们被鼓励去寻找那些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制定高远的目标,敢于失败,敢于再次尝试,同时也要及时庆祝成就。他们知道自己的声音很重要,他们可以带来不同,别人需要他们,而且他们也需要别人。
在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每周三都去到校外花两个小时上一门叫作“责任”的课。孩子们和自己的导师商量,找到一种既能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又能同时学到东西的活动。他们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有的在老人院工作,有的去幼儿园组织校园戏剧演出,一切由兴趣和学习目标决定。孩子们体验到了采取主动、被需要和在他人生活中带来不同是什么感受。
在八、九、十年级,学生会上一门叫作“挑战”的课,这个词在德语中很美,原意是“受到召唤,由内而外地生长”。他们被邀请发掘自己隐藏很深的内在潜力。
在这一学年中,他们会组织并参加一个特殊的三周活动,单独或以小组的形式挑战自己,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有个四人小组准备了一个三周的丛林生存营,他们在自己搭建的棚屋里靠采集的食物生活。丹尼尔是一个16岁的外向男孩,他的挑战是在一座寺庙里进行三周的止语禅修。一位音乐教师挑战一组孩子,让他们在一个废弃的旧农场里连续三周、每天8个小时进行高强度音乐训练。也有同学用极少的钱在德国骑行,路上吃住都需要请求别人提供。这种经历往往充满艰辛,但当学生们谈起他们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恐惧和超越恐惧所带来的个人成长时,兴奋与自豪溢于言表。
学生、老师、家长都在自主管理
学生、老师、家长都在自主管理
目前,ESBZ在学生自主管理方面最为大胆的尝试正在进行之中。在德国,十二年级末的学生必须参加全国高考,考试分数决定他们可以申请哪所大学。这次考试如此关键,因此,连ESBZ的十、十一和十二年级在过去几年中都一直依赖更传统的应试方法来教学。但同时,学生和教师们也在想, 有没有可能重新设计十、十一、十二年级的课程,使之既符合学校的指导原则又能帮助大家很好地备战高考?
今年,三个年级的所有学生会投入到这个雄心勃勃的一年期项目当中,重新设计三个年级的课程。设计思维方面的专家会通过一个两天的设计工作坊帮助师生一起开发出总体概念;然后,学生和教师会在顶尖教育专家的支持下,把这个概念变成具体的结构和做法。学生和老师正在高效地重新设计自己的学校。
ESBZ的教师也是自主管理的。教师通常是一个孤独的职业,而在ESBZ,教学是一个团队项目。每个班有两名导师,因此每个老师都在双人小组中;三个班组成一个迷你学校,他们在同一楼层工作,共用一个教师办公室,每周开例会。这些迷你学校就像FAVI、博组客或AES(著名的青色组织)的团队,能够对日常问题和机会做出快速的反应。表面上看,这所学校也有传统的层级(由于是政府出资,因此也必须设置一位校长、两位副校长和一位教学总监),但迷你学校不需校长批准几乎可以做所有的决定。
家长也是自主管理。学校的建立基于一个特殊条件:市政府仅支付教师工资的93%,而不支付有关教学楼和任何其他方面的费用。因此,家长需要按照家庭收入的比例捐款补齐费用缺口。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家长们决定每人每月贡献3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他们做什么和如何做都要遵循自主管理原则。
例如,教学楼整修团队经常定期组织大型欢乐周末活动,由50名家长动手翻新教室。几年前破旧、漏水的老楼房在家长们的努力下,变成一间间温暖、多彩、功能齐全的教学场所。放学之后,这里还会为从各地赶来学习ESBZ“魔法”的几百名校长和教师举办工作坊。你可能已经猜到,这些工作坊几乎全部都由学生带领,而非由教师或学校的创始人兼校长玛格丽特•拉斯菲尔德亲自讲授。
ESBZ值得关注的是它并不享受任何特殊的待遇。它与柏林其他任何学校一样必须满足定量的学时,并且即使有家长的捐款,学校的预算还是会比公立学校低。每一所学校都可以复制ESBZ的成功,因为更多的钱和资源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起作用的是用崭新的眼光来看待孩子、教师、家长和教育。
青色组织,所有的声音都有分量
文 /[美] 罗德• 柯林斯
由于有了互联网,于是有了新的世界观,并且它正在彻底转变我们打造组织的方式。依据弗里德里克•拉卢,即《重塑组织:进化型组织的创建之道》一书作者的观点,自上而下分级而治的主要组织架构已经时日无多,科技的革命释放了无与伦比且势不可当的遍布式智慧,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
拉卢使用颜色标记的类型学,概括了在过去一万年中,四种不同类型的组织的进化过程,并且详细地描述了下一个截然不同的新兴组织类型所具备的属性及特点。在人类的文明历程中,一共经历了四个模式,红色、琥珀色、橙色和绿色,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老板。从第一位部族首领到现代的首席执行官
(CEO),权力的行使方式一直是“掌控”。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人掌控,组织将如何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四个模式中,每一个都有些自上而下的层次结构形态。
但是,拉卢问:“我们是否能创建一个不需要被授权的组织结构?因为每个人天生都是强有力的, 没有人是毫无力量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创建一种组织,在其中,权责不再挂钩,那么,是不是就没有老板了?拉卢认为,这个答案就是青色组织。
青色组织是一种革命性的新型管理模式,其运行的前提是将组织视为有机生命体。因此,职能就更像复杂的自适应系统,而非机器。因此,这种组织形式是灵活和流畅的同伴关系结构,而工作则通过自我管理的团队完成。在青色组织中,没有中层管理层,只有很少的工作人员,以及极少的规则或管控机制。人们不再向某个主管报告,而是向他们团队的成员负责,以实现自组织的共同目标。这跟我们的直觉刚好相反,控制型老板的缺席往往能够生成一个更可控的组织,因为,拉卢指出,“同辈压力对系统的调节作用比等级结构更好”。
在这个组织里,每个人都是管理者。因为每个人都对其完成工作所需的资源,以及促使同事实现公司的使命负责。虽然青色组织中没有老板,但并不等同于无企业领导。事实上,青色组织比采取层级管理的类似组织要有更多的领导。
在这个组织里,所有的声音都有分量,因为任何人都能够感知问题或机会。由于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领导者,每个人都有能力招募追随者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行动。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加入,则行动就会发生;如果招不到队员,则什么都不做。与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相比,精心设计的同伴网络如此高效的原因,是它利用其集体智慧来响应快速变化的环境所带来的强大资源的这种固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