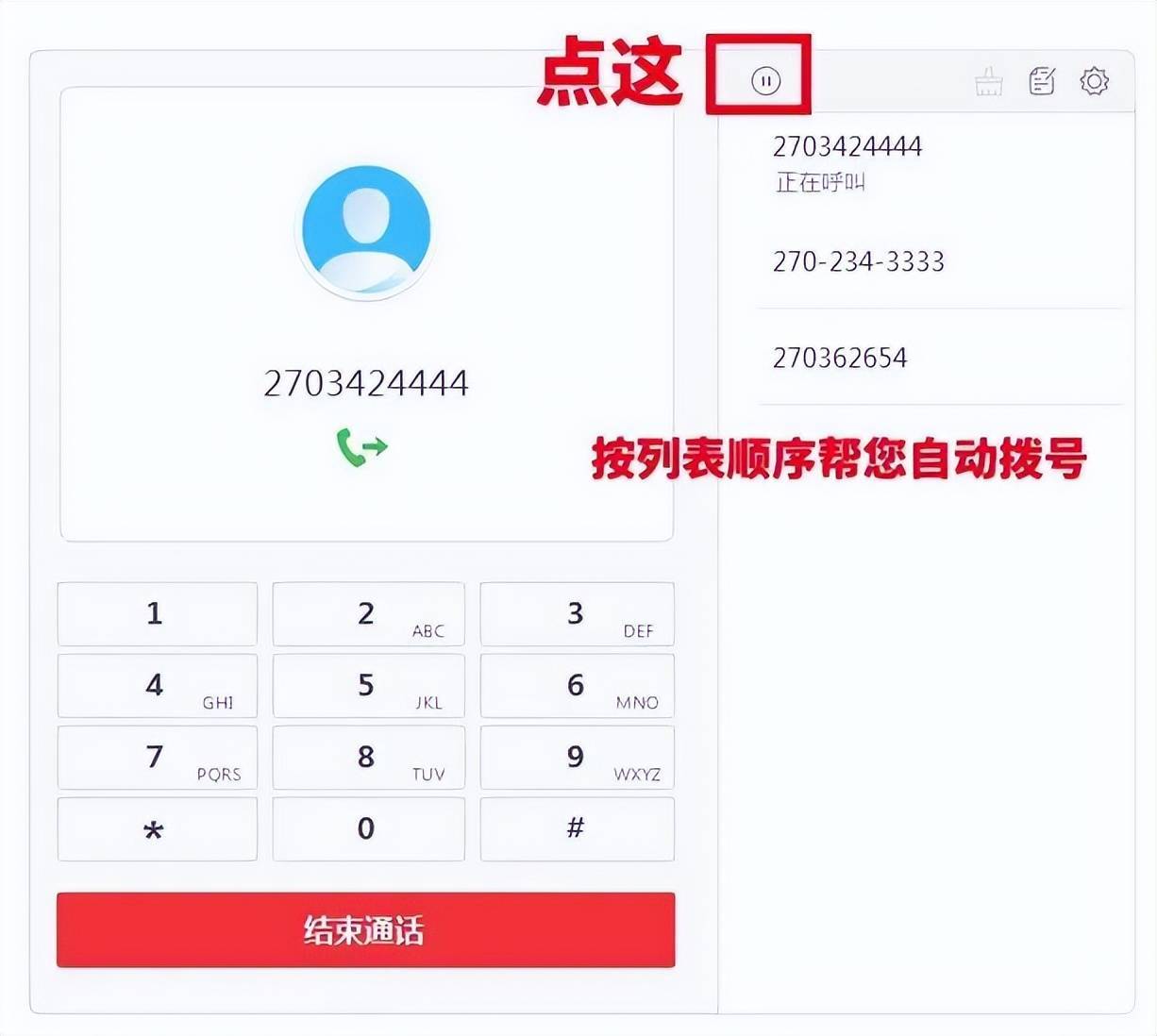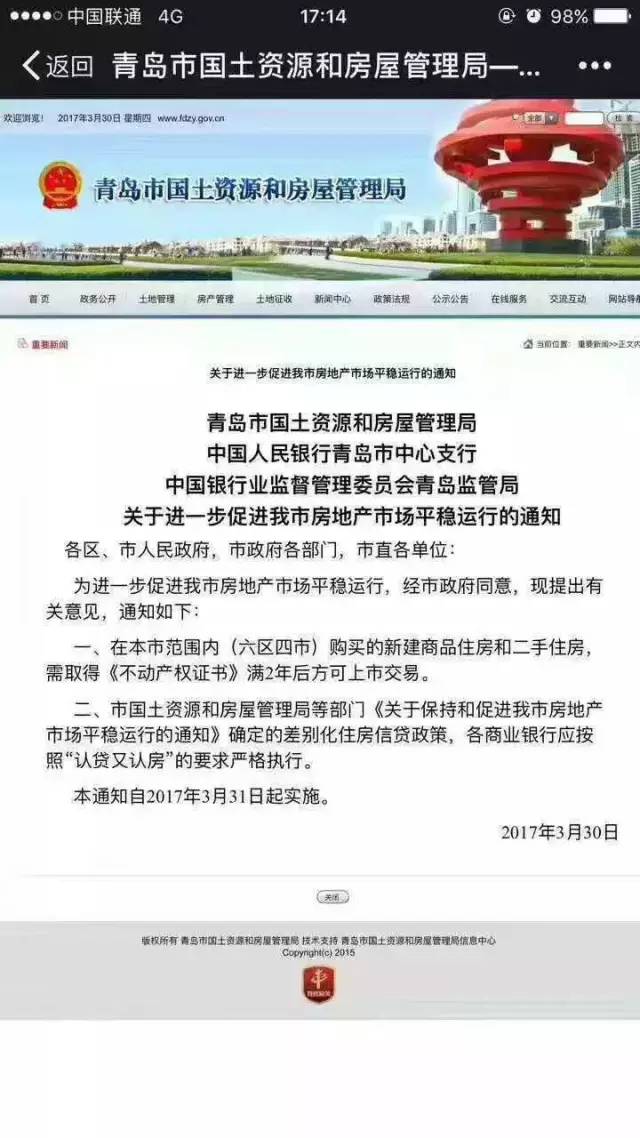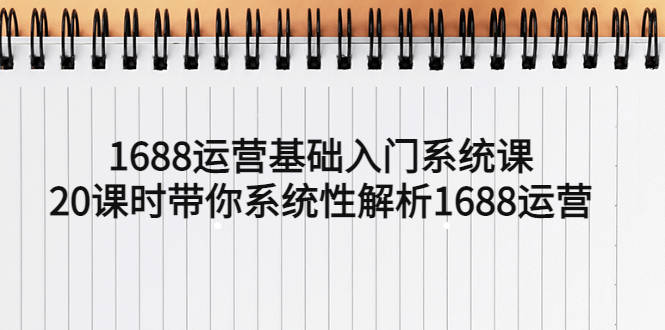《聊斋·宦娘》超越情欲的百年女鬼,谙筝喜琴的绝世良缘
《宦娘》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讲述女鬼宦娘对琴艺高超的温如春有情,但人鬼殊途,不能结合,为酬谢温如春的授琴之恩,促成其与世家小姐良工的美好姻缘。
《宦娘》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讲述女鬼宦娘对琴艺高超的温如春有情,但人鬼殊途,不能结合,为酬谢温如春的授琴之恩,促成其与世家小姐良工的美好姻缘。

《宦娘》这篇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没有电闪雷鸣般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震撼人心的灵魂搏斗。它只是写酷爱音乐的三位男女青年结成师友和夫妇的故事。事情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但作者却把它写得富有传奇色彩,情节发展波澜迭起,朦胧迷离,像一首轻灵的抒情曲,一首古老的叙事民歌,一篇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哲理性的思考。
《宦娘》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是巧用悬念,推进情节、表现人物性格,蒲松龄和许多文艺大师一样,在作品中常常给人留有想象和再创造的余地、不把什么都说完说尽,而是采用明暗结合的方法,给人们留有想象的广阔天地,诱导读者对作品中人物、事件、场景作出合乎情理的想象补充,完成作品的最后创造。
暗写,是一种间接的描写手法,它对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有意识地不让人物出场,使读者在事件发生的当时,看不到其人的存在和活动,给人们留下强烈的悬念,从而激起读者急于往下读的热情。适当时候转入明写,点明其中奥秘,读者才恍然大悟﹐然后对作者有意不写出的部分进行想象补充,从而获得极大的艺术满足,《宦娘》就是采用明写与暗写结合的写法,巧留悬念获得成功的作品。

小说开头明写温如春从古寺向布衲道人学艺归家途中,忽遇暴雨,天又黑了,便急匆匆走进路旁小村一个院子里避雨,不见一人。忽然一女郎走出,其貌美若天仙,抬头见有陌生客人,“惊而走入”。后来出来一老妪,方知那女子是她侄女,名叫宦娘。
温如春大胆求婚,遭老妪拒绝,他只好在腐湿的秸草上“危坐鼓琴”,以排遣郁闷,度过漫漫长夜。雨停后他便回家,宦娘也不再露面,就此消失了。
作者对此按下不表,却转入写温如春向葛良工求婚并由此产生一系列奇怪现象:温如春回家后,某次偶然去拜访葛家﹐受命弹琴,葛女良工窃听,对温倾慕。

温如春见良工“丽绝一世”,又“善词赋,有艳名”,忻然前去求婚。但因出身寒微,遭葛父拒绝。婚事无望,由此消沉、不再登葛家之门。岂知这时在温、葛两家之间却发生了几件怪事:
一是良工在花园中拾到一首委婉缠绵、倾诉爱情的《惜余春》词,引起共鸣,拿回闺房“庄书一通”,放置案间,不一会就找不见了,却被葛父在门外拾去。葛父恼恨这词写得淫荡,以为是女儿怀春之作,便急欲把女儿嫁出。
二是正在这时,有钱有势的刘家公子前来求婚,葛父喜其“仪容秀美”,准备答应。后因在其座位下发现遗下女子绣花鞋一只,讨厌其为人轻薄,便绝了这门亲事。
三是一向只有葛家有绿菊种,种在良工闺房,从不外传。温家的菊花忽然有一、二株化为绿种,葛父闻讯前去观赏,正巧在温如春书房里看到温拾到的同一首《惜余春》词,遂疑词、菊均为女儿良工所赠。

这三件奇事如果外传,定然损害葛家声誉。葛母力主把女儿嫁给温如春,葛父恐家丑外扬,只好答应。这几件怪事的来龙去脉无影无踪,给人以迷离恍惚、神秘莫测之感。
读者读至此,不能不感到迷惑不解,猜测其中奥秘。这一系列离奇古怪的事件和宦娘有什么瓜葛?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怪事?是偶然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神灵相助?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有如堕入五里雾中。
既然篇名《宦娘》,何故宦娘只露一面就销声匿迹?作者是何用意?这种紧紧吊住读者胃口的悬念的艺术处理,正是作者运用暗写的高明之处。直到温如春、葛良工结婚以后,互诉衷情,方知二人得以结合之原因。但仍不知是何人所为。
其后笔锋突转,写夜间琴声自鸣,良工借来古镜鉴照,原来是女鬼宦娘在学琴。开头失踪了甚久的宦娘突然出现,这才把谜底揭开。原来上述种种怪事乃是宦娘为报温如春眷顾之情,用其鬼神之功制造出来以促成如春、良工婚事的。

这一主体情节,明写如春、良工爱情纠葛,暗写宦娘情怀及其高尚情操,她虽不露面,但却若隐若现,无处不有其影子在。如果离开了宦娘,这段情节则难以发展,温如春和葛良工的爱情只能夭折。而末了的人鬼之间相互听琴、弹琴学筝等尾声也就失去了依据。这里值得提起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暗写,既不能直露,也不能一味求简,过于隐蔽。它应当是写得极有分寸,给读者留有思索想象的空白,又能为读者对艺术形象进行想象补充提供线索和暗示。
《宦娘》的成功在于开头的明写,点出人物,中间暗写留下悬念,结尾的明写抖开包袱﹐解除悬念,当我们读到最后,掩卷深思,就会感到宦娘的魅力。
看过曹禺的《日出》,也会发现小说中写了一个不出场的人物金八,尽管金八没有露面、却声色俱厉地制造着陈白露、小东西等人的悲剧他的名字不断地在剧中出现,但并未成为作品的主要人物、对他虽用“暗写”,但剧中人和观众却自始至终无时无刻无不感觉到他的存在和威势,不似官娘这样给人留下联想的广阔天地。

用“琴”串起全篇结构是《宦娘》艺术构思的特色。“以琴起,以琴结、豚络贯通,始终一线”,写琴是为了写人,琴和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带起情节发展,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针线绵密﹐开头点出主人公温如春“少癖嗜琴”,伏下全篇线索。
“琴”,成为联系一系列人物和情节发展的红线。因温如春嗜琴,引出他和精于琴艺的布衲道人的一段交往,因道人琴艺超群,达到“才拨动”便“和风自来”,以至“百鸟群集,庭树为满”的奇妙境界,温遂拜道人为师,学成绝技。
后来在归途中遇雨,暮宿宦娘家,因人鬼异路,求婚遭拒,乃危坐鼓琴,抒发愁绪。由于他的奇妙琴声,为自幼喜琴的宦娘倾倒,乃暗中与温结成纯真的师生关系。
同样,由于温之善琴,又引起有相同爱好的葛女良工倾慕,由于葛父嫌贫爱富,二人婚事不谐。后在宦娘暗中帮助下二人遂结连理。如春、良工婚后,宦娘方现形求温“曲陈其法”,使她尽得操琴“神理”﹔又因宦娘善筝,成了喜筝的良工的业师。
最后宦娘留下小象一卷,希望温、葛夫妇快意时“焚香一炷,对鼓一曲”则心满意足了,说罢悄然离去。小说以琴起头,以琴串起全篇情节,又以琴结尾,脉络贯通,结构十分严谨。

读完《宦娘》,仿佛有一位貌若天仙的女鬼在眼前恍动,她温柔、贤慧、多情,自幼酷爱音乐,谙筝喜琴,可惜未得嫡传,琴艺未精,她向往人生,渴求爱情,对温如春也倾心爱慕,只因人鬼隔世,不能结合。只好“因恨成痴,转思作想”、“甚得新愁旧愁”,“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
剩下的那就是“蹙损春山,望穿秋水”,“芳衾妒梦,玉漏惊魂”了。一曲《惜余春》词,字字有泪,句句含情,写得哀婉缠绵,如泣如诉,能说不是她饮恨九泉,伤心薄命,借题抒发她的情怀吗?但她强忍着内心的痛苦,为了促成温葛婚姻,她细察葛父举动,捉弄了刘公子,出没在温葛庭园之中,往来于如春、良工之间,穿针引线。
我们似乎看到她夜以继日,风尘仆仆,不停地奔波,呕心沥血,巧计安排,终于促使封建门阀观念极深的葛父改变主意﹐使如春、良工结成佳偶,以报温对她眷顾之情。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她有一副美丽的外表,而且可以窥探到她那一颗颤动不已、凄恻伤感、温厚美好的心灵。她在《聊斋》的众多女性形象中独放异彩,令人难忘。
《宦娘》原著:
温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虽逆旅未尝暂舍。客晋,经由古寺,系马门外,暂憩止。入则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间,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温触所好,因问:“亦善此也?”道人云:“顾不能工,愿就善者学之耳。”遂脱囊授温,视之,纹理佳妙,略一勾拨,清越异常。喜为抚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许可。温乃竭尽所长,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足为贫道师也。”温以其言夸,转请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拨动,觉和风自来;又顷之,百鸟群集,庭树为满。温惊极,拜请受业。道人三复之,温侧耳倾心,稍稍会其节奏。道人试使弹,点正疏节,曰:“此尘间已无对矣。”温由是精心刻画,遂称绝技。
后归程,离家数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村,趋之,不遑审择,见一门匆匆遽入。登其堂,阒无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类神仙。举首见客,惊而走入。温时未偶,系情殊深。俄一老妪出问客,温道姓名,兼求寄宿。妪言:“宿当不妨,但少床榻;不嫌屈体,便可藉藁。”少旋以烛来,展草铺地,意良殷。问其姓氏,答云:“赵姓。”又问:“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犹子也。”温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系,如何?”妪颦蹙曰:“此即不敢应命。”温诘其故,但云难言,怅然遂罢。妪既去,温视藉草腐湿,不堪卧处,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夜遂归。
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温偶诣之,受命弹琴。帘内隐约有眷客窥听,忽风动帘开,见一及笄人,丽绝一世。盖公有一女,小字良工,善词赋,有艳名。温心动,归与母言,媒通之,而葛以温势式微不许。然女自闻琴以后,心窃倾慕,每冀再聆雅奏;而温以姻事不谐,志乖意沮,绝迹于葛氏之门矣。一日,女于园中拾得旧笺一折,上书《惜余春词》云:“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铲尽还生,便如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今日个蹙损春山,望穿秋水,道弃已拚弃了!芳衾妒梦,玉漏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侬视一年,比更犹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咏数四,心悦好之。怀归,出锦笺,庄书一通置案间,逾时索之不可得,窃意为风飘去。适葛经闺门过,拾之;谓良工作,恶其词荡,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醮之。临邑刘方伯之公子,适来问名,心善之,而犹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仪容秀美。葛大悦,款延优渥。既而告别,坐下遗女舄一钩。心顿恶其儇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辩其诬,葛弗听,卒绝之。
先是,葛有绿菊种,吝不传,良工以植闺中。温庭菊忽有一二株化为绿,同人闻之,辄造庐观赏,温亦宝之。凌晨趋视,于畦畔得笺写《惜余春词》,反覆披读,不知其所自至。以“春”为己名益惑之,即案头细加丹黄,评语亵嫚。适葛闻温菊变绿,讶之,躬诣其斋,见词便取展读。温以其评亵,夺而挼莎之。葛仅读一两句,盖即闺门所拾者也。大疑,并绿菊之种,亦猜良工所赠。归告夫人,使逼诘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无验见,莫有取实。夫人恐其迹益彰,计不如以女归温。葛然之,遥致温,温喜极。是日招客为绿菊之宴,焚香弹琴,良夜方罢。既归寝,斋童闻琴自作声,初以为僚仆之戏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温。温自诣之,果不妄。其声梗涩,似将效己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无所见。温携琴去,则终夜寂然。因意为狐,固知其愿拜门墙也者,遂每夕为奏一曲,而设弦任操若师,夜夜潜伏听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听闻。
温既亲迎,各述曩词,始知缔好之由,而终不知所由来。良工闻琴鸣之异,往听之,曰:“此非狐也,调凄楚,有鬼声。”温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镜,可鉴魑魅。翌日遣人取至,伺琴声既作,握镜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仓皇室隅,莫能复隐,细审之赵氏之宦娘也。大骇,穷诘之。泫然曰:“代作蹇修,不为无德,何相逼之甚也?”温请去镜,约勿避;诺之。乃囊镜。女遥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筝,筝已颇能谙之,独此技未能嫡传,重泉犹以为憾。惠顾时,得聆雅奏,倾心向往;又恨以异物不能奉裳衣,阴为君吻合佳偶,以报眷顾之情。刘公子之女舄,《惜余春》之俚词,皆妾为之也。酬师者不可谓不劳矣。”夫妻咸拜谢之。宦娘曰:“君之业,妾思过半矣,但未尽其神理,请为妾再鼓之。”温如其请,又曲陈其法。宦娘大悦曰:“妾已尽得之矣!”乃起辞欲去。良工故善稳,闻其所长,愿以披聆。宦娘不辞,其调其谱,并非尘世所能。良工击节,转请受业。女命笔为给谱十八章,又起告别。夫妻挽之良苦,宦娘凄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乌有此福。如有缘,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温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当悬之卧室,快意时焚香一炷,对鼓一曲,则儿身受之矣。”出门遂没。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关注遥山书雁,带您领略文化的博大精深!
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