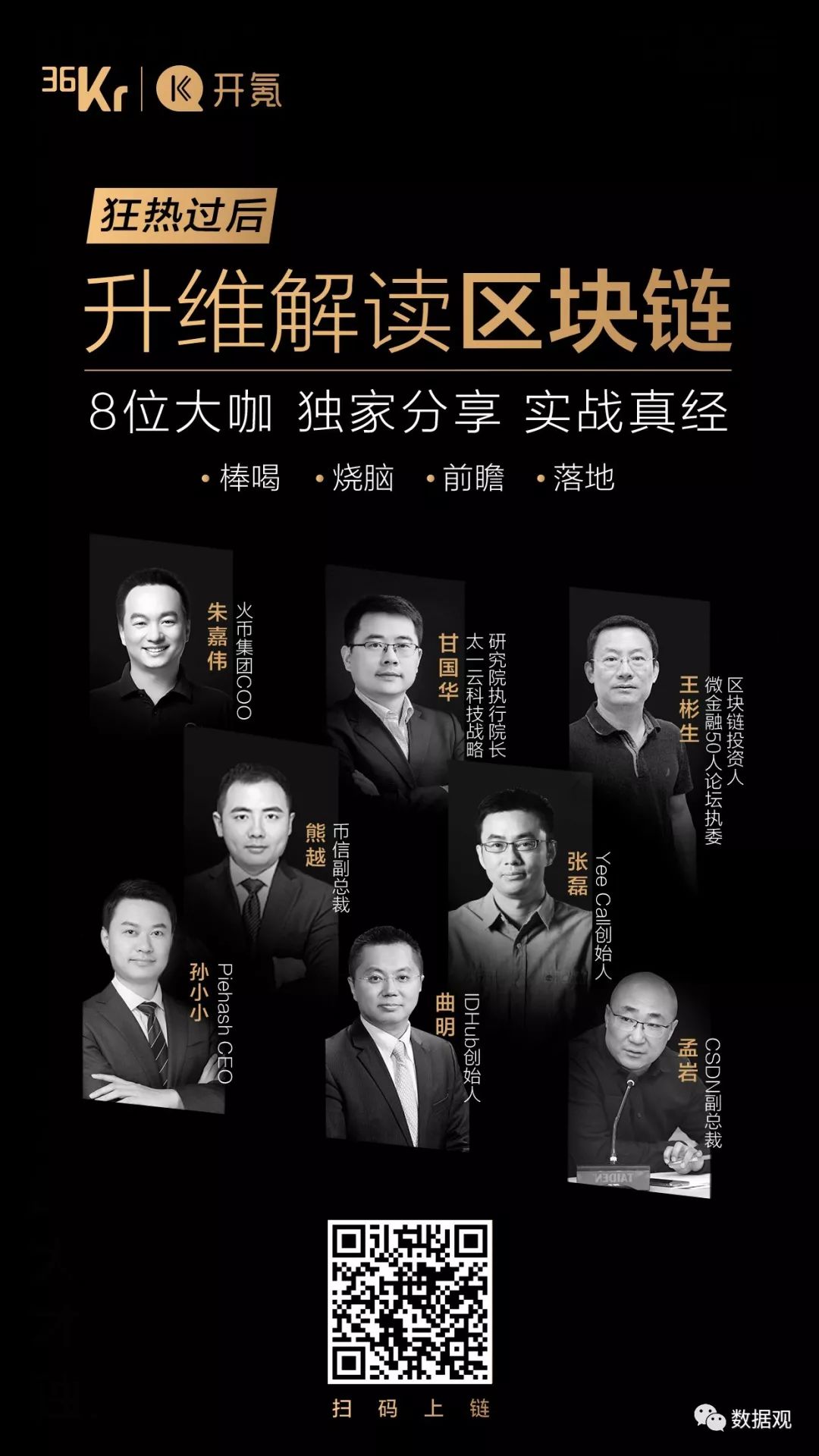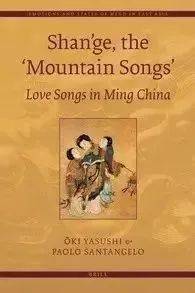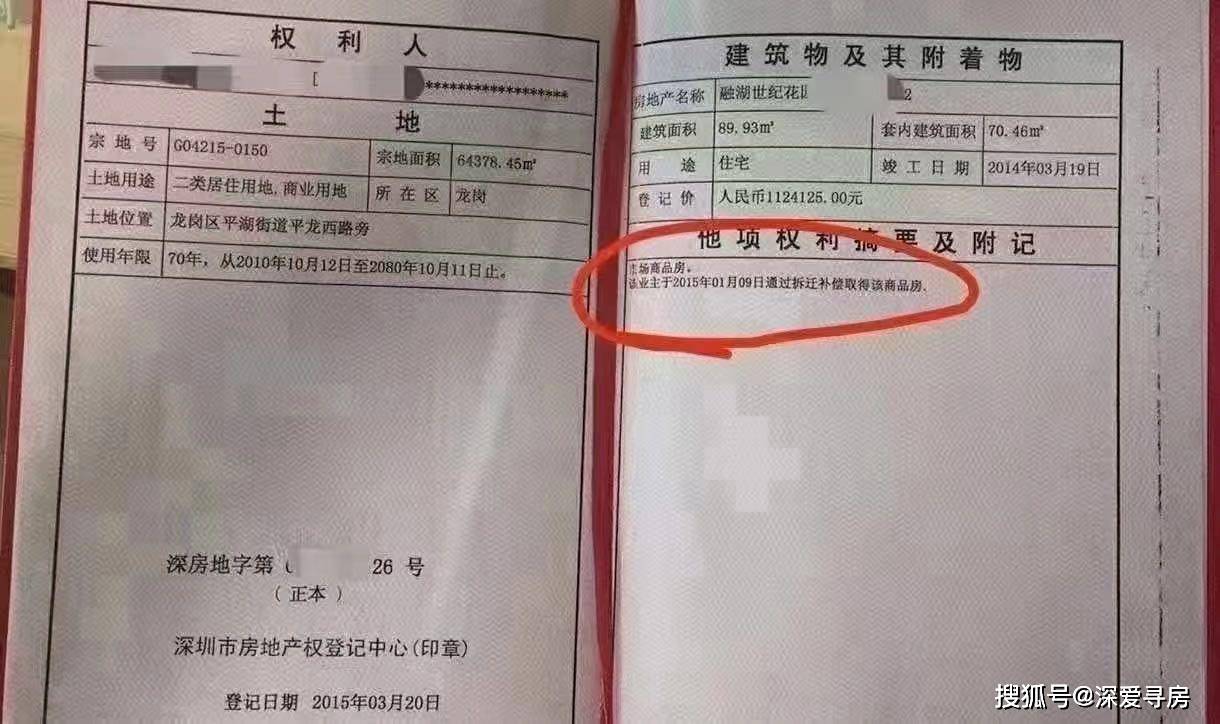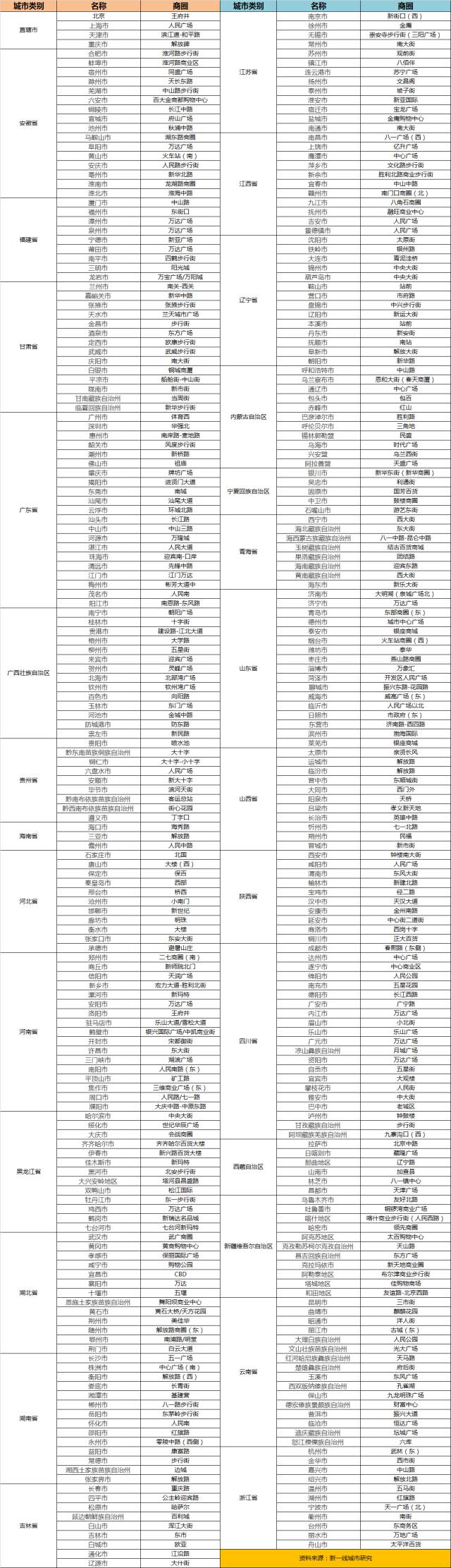杜义德
(1912年5月10日—2009年9月5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海军第二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
爸爸和奶奶的故事
作者:杜红
爸爸叫杜义德,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塔尔镇柿子村店陈家嘴村(现为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也就是湖北木兰山一带。奶奶叫柳华山,听说嫁给爷爷后一连生了七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有五个,三男两女。爸爸是小儿子,排行老四,小名三娃子。
1
爸爸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爷爷靠租种胡家湾大地主的地来维持一家八九口人糠菜半饱的日子,奶奶娘家的家境稍微好点,资助爸爸读了几年私塾,这成为爸爸日后走向革命迅速提高文化和军事水平的基础。1927年爸爸参加了农民协会,1928年参加农民赤卫军,到1929年转为中国工农红军,这一年,爸爸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疼爱他的父母,一走就是近20年。
爸爸参加红军后不久后地主还乡团回来了,把爷爷骗到县里,逼着爷爷交出爸爸,爷爷被打得皮开肉绽,乡亲们把他抬回家后没几天就咽气了。与爸爸一起参加赤卫队的一个同村小伙伴跑回家看父母,半路被还乡团抓住残忍的剖腹示众。奶奶托人捎口信给爸爸:“不要回来,为你爹报仇!”之后,她孤寡一人带着大伯、二伯和两个姑姑,白天下地劳作,晚上纺纱、织布、编草鞋,逢集叫卖土布草鞋,艰辛地维持着生计。
1947年冬季,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爸爸随部队打回大别山,攻下黄陂,那时他已经是第二野战军第六纵队的政委了。腊月二十九,临近过年的一个夜晚,爸爸带着一个骑兵排的战士,回到了阔别18年的家乡,见到了他久违的老母亲——我的奶奶。是夜,那么黑,那么静,爸爸凭着记忆找到了奶奶住的破旧土屋,推开门,昏暗的油灯下奶奶正在纺线。奶奶闻声抬头,看到几个持枪的军人,吓得浑身发抖,爸爸忙摘下帽子,说:“妈,我是三娃子!”离家时十几岁羸弱的三娃儿,如今成了气宇轩昂的军人!奶奶恍惚在梦中,难以置信,愣了好一会儿,才又喜极而泣。那夜,爸爸对奶奶说:“妈,等打完了敌人,我就回来接你。”
解放后,爸爸把奶奶从老家接出来,一起随军生活。后来,无论是爸爸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还是抗美援朝期间,全家几度搬迁,奶奶一直没有回乡,跟着爸爸和妈妈一起生活。那时候,奶奶膝下孙儿女满堂,爸爸很少外出应酬,一日三餐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那是我们一家人最温暖快乐的一段回忆。当年饱经沧桑瘦弱的奶奶也渐渐地丰润了起来,慈爱的笑容渲染着全家人祥和的气氛。
2
小脚奶奶是家庭最高权威,爸爸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大将军爸爸对奶奶唯命是从、毕恭毕敬,孙儿们学着爸爸也格外的尊重奶奶,整日围着奶奶转,想法儿逗着奶奶乐。
那时候爸爸妈妈的工资不高,要赡养奶奶和七个孩子,要接济老家生活在贫困线的伯伯姑姑们,家里经济上常常是捉襟见肘,孩子们也是鲜有新衣。记得那会儿家里餐桌上少油寡荤,过生日才能吃两个鸡蛋,小学春游的时候其他同学带面包,我们只能带馒头干加咸菜。尽管如此,爸爸总会特别照顾奶奶,常给奶奶特供糕点、糖果。我记得奶奶有顶漂亮金丝绒的帽子、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还有个古香古色的五斗橱和一座棕色实木座钟。
奶奶最喜欢四姐小宁(后来才发现小时候的四姐像极了爸爸),常常把四姐叫到自己房间,关上门偷偷给她吃糖果蛋糕,把个四孙女宠得白白胖胖的。
这样,自1949年起,奶奶和她的三娃子一家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好日子。
3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爸受到了冲击,一个曾经为党和人民枪林弹雨鞠躬尽瘁几十年的开国将军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三反分子”,家里几度被造反派抄家,楼里楼外贴满了“打倒三反分子杜义德”的大字报,爸爸珍藏的许多历史文物和字画也渐渐地遗失了。
一次,几个造反派到家里组织全家老少开家庭会议,要奶奶给爸爸忆苦思甜。年近九旬的奶奶思路清晰,她淡淡地对造反派说:“我现在听到你们敲门的声音,就想起了当年还乡团来我家抄家和烧毁房子的往事……”造反派听罢,张口结舌。
抄家的造反派走了,家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竟然是一片狼籍。奶奶伤心不解地对爸爸说:“你革命了那么多年,怎么还成了反革命?为了你革命,你爸爸也被地主还乡团给打死了,现在又要打倒你,我还不如回老家去。”爸爸满怀歉意地说:“妈,让您老人家受委屈了。相信儿子,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反革命、三反分子。”
4
1969年9月,爸爸被送到江西上饶“劳改”,临走那天,母子俩执手相送,奶奶忍不住哭了。
奶奶对爸爸说:“过些天,你大哥秋收完了,就来北京接我回去。”
爸爸无可奈何地对奶奶说:“等把问题搞清了,我再把妈妈接来。”
爸爸走的那天,奶奶扶着门,站在那里望了又望,久久不愿回屋。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是爸爸和奶奶的永别!
不久,大伯忙完秋收后赶到北京,接走了和我们一家一起生活了20年的奶奶,孙儿泣,母亲泪,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奶奶了。
5
1969年这一年,家里三个年纪大的姐姐们赴内蒙、陕西、天津农村插队,我们四个年幼的孩子们随着妈妈到江西上饶市与爸爸团聚,随后又去了浙江江山县。1971年“913事件”后,妈妈回京四处上访,为父亲争取复职。1972年初,经军委批准,海军同意爸爸带家眷回京,2月份派人到江山县接我们。
就在全家收拾行装准备回京的时候,爸爸收到了老家电报,奶奶病危了,嘴里不断地喊着爸爸的小名,道着心中的思念和冤屈……
一方是组织的召唤,丧失工作权利五年的爸爸要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为党、为国家、为海军建设效力了;另一方是奶奶的临终呼唤,像针刺一样的母子亲情眷恋。
记得收到电报的那天晚上,我们小孩子们特别乖巧,轻声轻脚的,生怕惊扰了心情沉重的爸爸。我路过爸爸的房间,门是半遮掩的,屋里一片漆黑,只听到爸爸踱步的声音。爸爸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手中烟头的闪着微光,窗外的月光洒在他高大的身躯上,久久不出一声……
那些日子,爸爸少言寡语,孩子们也格外老实听话。最终,爸爸选择了如期返回北京,听从党组织的召唤,奔向他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革命事业。
那一年,爸爸61岁。
6
回京不久,全家被安排在校级楼房,爸爸还没戴上领章帽徽,就接到了老家来电——奶奶过世了。记得收到噩耗的那天,狭小的单元房里气氛格外凝重,四姐哇哇大哭,爸爸沉着脸,把自己久久的关在房间里……。
那日爸爸夜幕焦虑的场景我一直记着,当我长大懂事后,才明白父亲那时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煎熬,才明白父亲坚毅的性格除了来自战火的考验,还有无数次人性情感的磨砺!才明白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选择的艰难,还有老一辈革命家无可选择的艰难,而这无可选择的选择对一个重情重义的将军是多么的沉重!日后,当我走向社会时,每当面临着责任和情感的抉择,遇到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时,我常常会想起爸爸坚毅的面颊,想到那晚见到爸爸抉择的一幕。
奶奶过世后,爸爸一直没有回到老家,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爸爸退居二线后,开始频频回到湖北黄陂,为家乡的建设献计献策,我们孩子们也开始为家乡人捐献衣物。离开家乡近六十年的爸爸,每每回乡,定要去奶奶的墓前培土植树。
2009年9月5日,爸爸辞世,享年98岁,三年后我们将爸爸的塑像安放在他参加革命的起始地——湖北黄陂。从此,爸爸那坚定而慈祥的目光,永远注目着他亲爱的家乡,他和奶奶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湖北黄陂木兰乡。每年清明,我们总要派代表回老家给爸爸和奶奶扫墓。
7
从1969年我们和奶奶分别到现在,一晃四十多年了。我相信,爸爸此时已经和奶奶重逢了,在天上一个美丽的地方,唠叨着家常,微笑着看着我们,看着他们在人间的子子孙孙们。
有一天,我们也将与爸爸和奶奶在天上相聚,这一大家人啊,又能欢喜的聚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
希望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负爸爸和奶奶的教导和期望,交上一份让他们满意的人生作业。

1965年秋,奶奶、爸爸和三个大姐姐们在看弟弟们照相。从1949年起,奶奶和我们一家人度过了近二十年其乐融融的日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爸爸退居二线,开始频频回到老家湖北黄陂,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图为1996年3月,爸爸和妈妈给奶奶扫墓。
2009年9月5日,爸爸辞世,享年98岁,三年后我们将爸爸的塑像安放在他参加革命的起始地——湖北黄陂。83年后杜义德将军重归故里,他那坚定而慈祥的目光永远注目着他的家乡,他和奶奶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木兰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