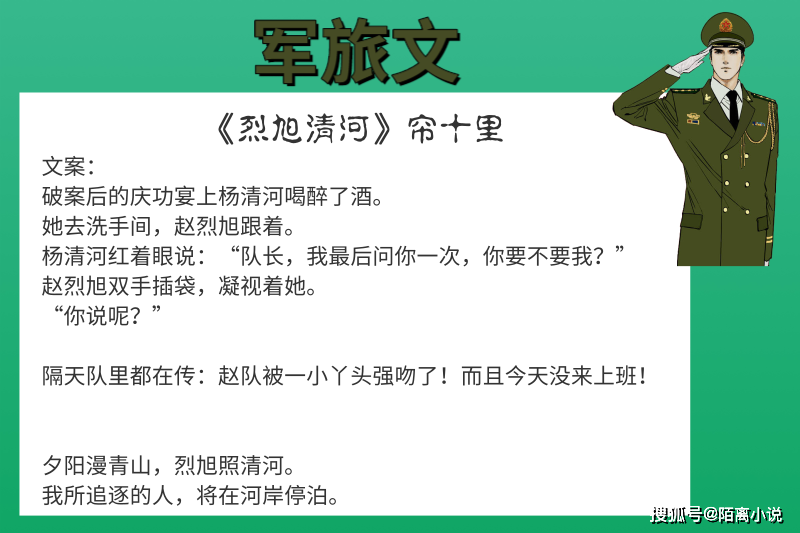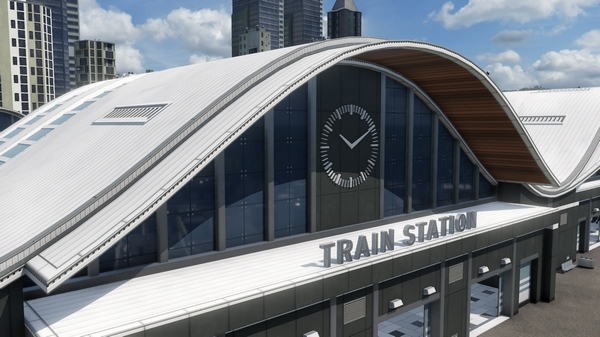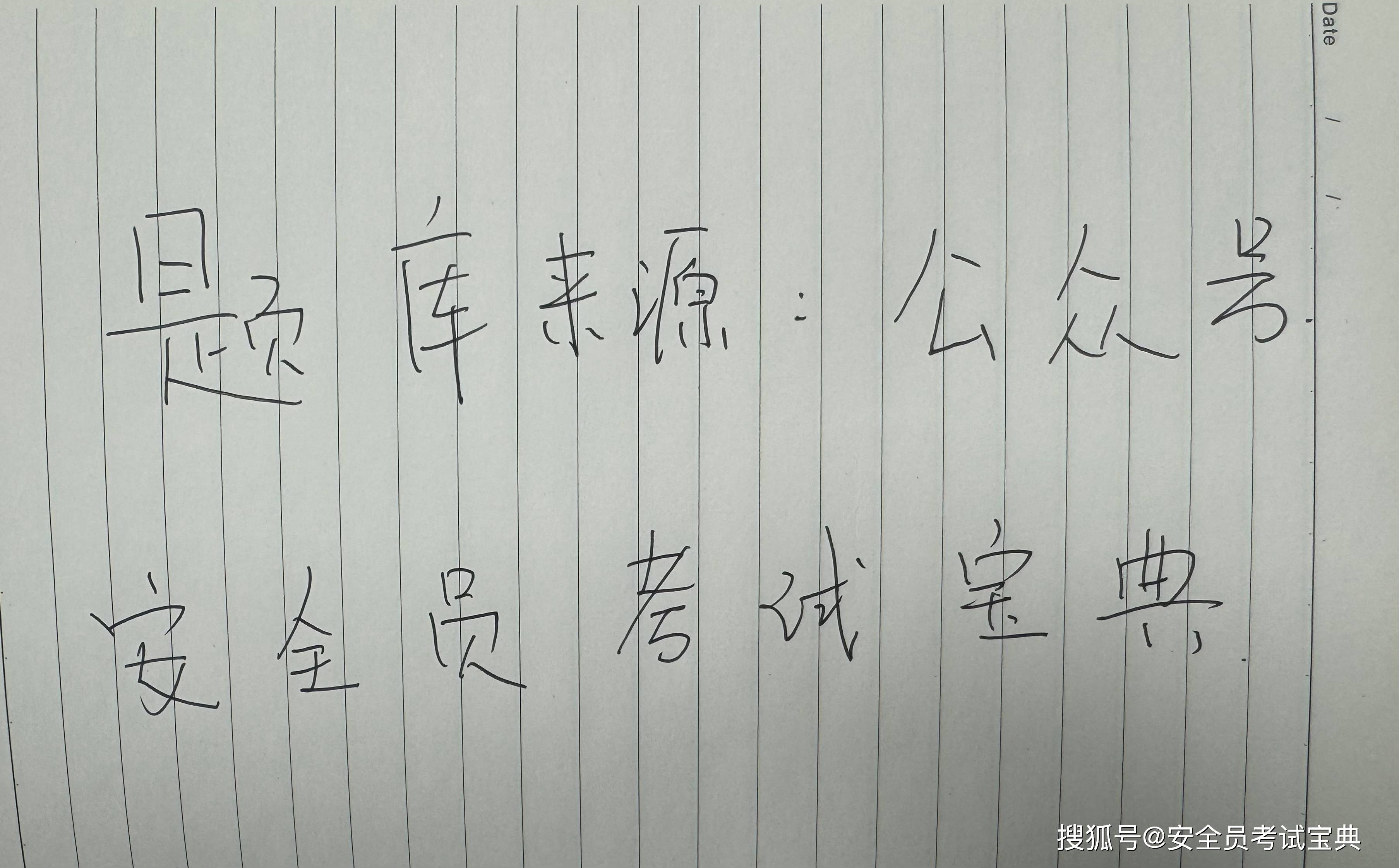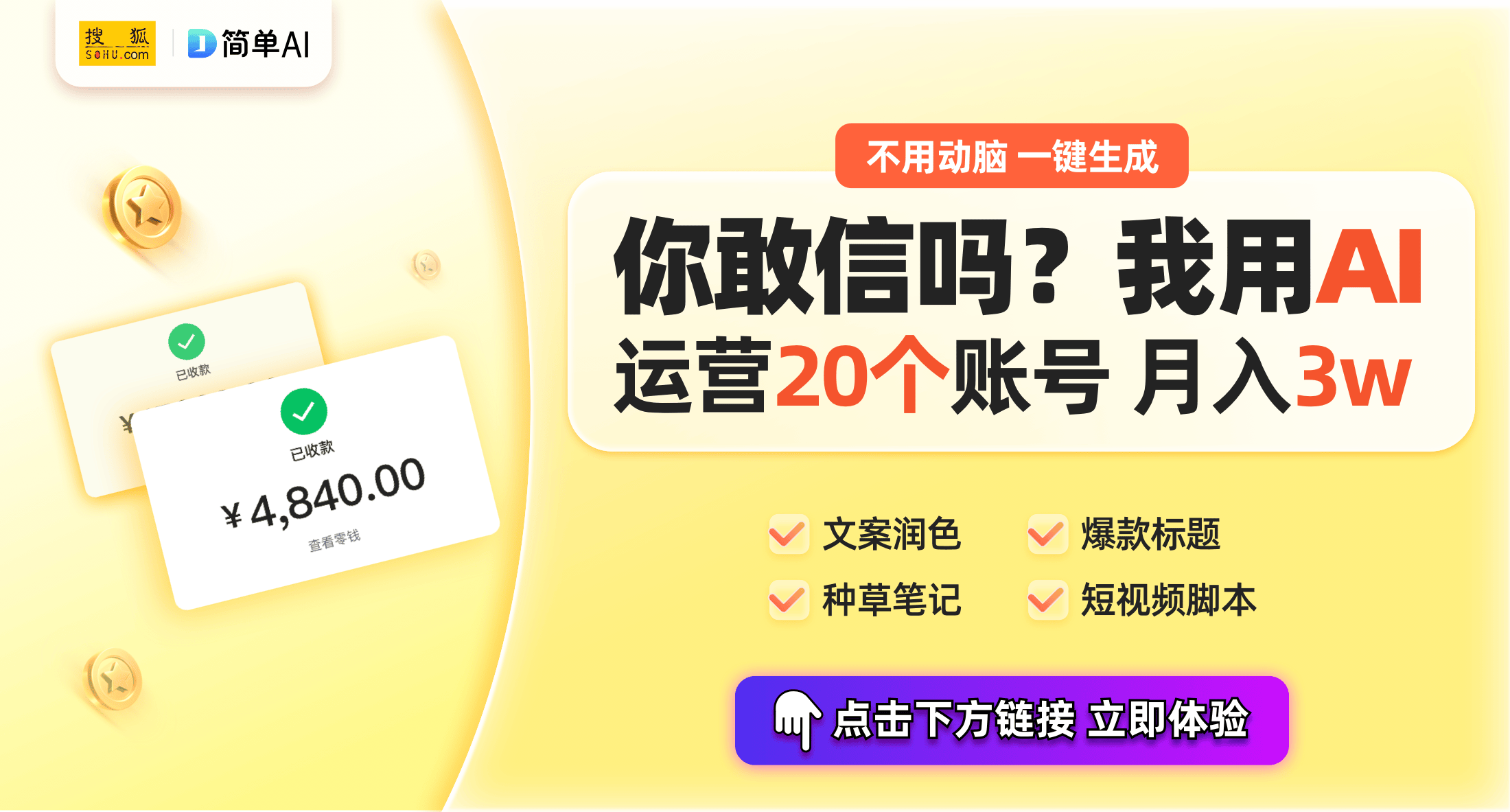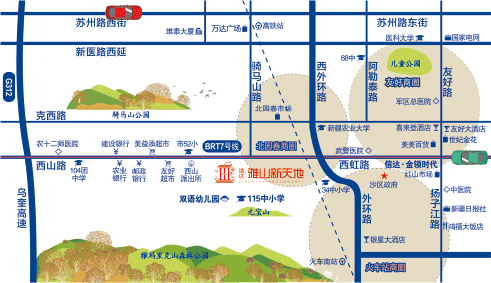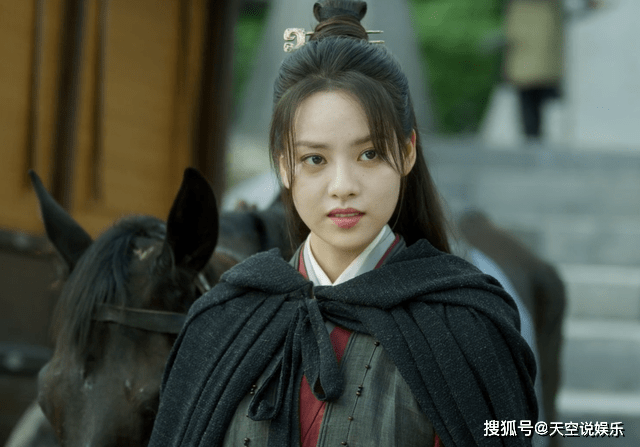为何远行
——为何远行?有一次我问友。
渴望战栗。他漫不经心地答道。我被狠狠“电”了一下,觉得这句话好极了,叫人沉默。
一个人,无论多么新鲜的生命,如果在一个生存点上搁置太久就会褪色、发馊、变质。感情就会疲倦,思想和呼吸即遭到压迫,反迟钝,目光呆滞,想象力如衰草般一天天矮下去......
法国诗人阿兰说:“对于忧郁者,我只有一句话,向远处看。如果眼睛自由了,头脑便是自由的。”
“出走”——可理解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私奔”,一种对现时生存秩序和栖居方式的反抗或突围。一股再忍下去即要发狂的激情炙烤着你,敦促和央求着你一冲出去!
从冒烟的牢房里冲出去。你是一吨炸药。否则就来不及了。
陈旧的生活总是令人厌恶和恐惧,只有陌生才会激起生命的亢奋与战栗。所以,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在路上”的行者,他总是将梦想盲目而执拗地撒向远方......
重要的是去,而非去何处。
渴望换种新的活法。渴望地理的改变能唤醒内心死去的东西。渴场一场烂漫的邂逅。渴望抚摸一棵叫不上名字的树......
渴望渴了能遇见一条清洁的河。
在神话典籍里——
“远方”是一条妩媚的、寂寞太久的狐。
她要有人去。特别是像山一样精纯的男子。在有月光的夜晚,走进她的林子。她睡了一千年,养足了温柔和血气,只待那个人来那与她有过一样的梦的旅者
只待那高潮战栗的一刻。
千年一刻!

刹那感觉
当列车启动,当城市峡谷和电视塔森冷的阴影、妖冶眩迷的霓虹灯招牌“呼”地像纸片般向后窜去……渐渐,车窗前方浮出蝌蚪般谦卑而亲蔼的灯火一清爽、温润,一点不刺眼,那是村寨的标识。影影绰绰,月光下,你看见了黛青的山廓和果冻似的湖。
隔着玻璃,它们送来了干净的风和植物的气息。稻畦、草叶、芦苇、池塘、蛙鸣、狗吠……幻觉里甚至还出现了更远的事物:林莽鹏、草丛间野兔疾电般的一跃。
那一刹,随着野兔的闪耀—一你浑身猛然一震。是战栗!是被照亮!一股不可遏制的暖流奔泻而出……久盼的湿润和舒畅。自由了的感觉。生命减轻后的感觉。
像一个越狱成功的囚徒,证实甩掉了跟踪和监视的感觉。
冲过来了!啊,千真万确。
伟大的豁亮的那一刹那。

从熟悉的生态圈闯出来,这意味着那些无形的“警戒线”和“纪律”像狱卒一样被干掉了——被时间和速度,悄无声息,手法干净利落。
列车长号一声,像脱缰的野马,在月光的婚床上,幸福地撒开蹄......
陌生的车厢。安全的车厢。
人人恋爱、自由清洁的车厢。
啊......愈来愈快,身子愈来愈快,愈来愈轻,愈来愈像那只兔子,那只闪电一样喷射高潮的兔子......
上帝的兔子!
你长长嘘出一口气,让肺里的淤泥彻底倒空—像一只旧抽屉来个底朝天。对,底朝天。
然后,你伸展躯肢,寻找最舒服的姿势,怎么舒服怎么做!
他们再也赶不上你了,你想。
他们正因失去管辖对象而气急败坏呢。
没有你,这些老爷们孩该怎么过啊......
想到这动人情景,你做坏事似的笑了。
让他们满世界找你去吧!
没有奴隶,他们就是奴隶了。
啊,生活......生活真好!

他们是谁?
他们是操纵程序的人。他们霸占某一城市、部门、单位……就像老鼠、蟑螂霸占一间旧屋和一只破麻袋。他们靠吮血为生,靠咬脏东西为生,靠窃取别人的劳动和撕碎愿望为生......
他们是虐待狂,一见别人挣扎就兴奋。
现在他们见不到了,于是现在轮到我高兴了。
他们不一定是人。但确有其人。
列车上的瓢虫
一粒火似的瓢虫,当欲去拉窗的时候,踩着了我的视线。
显然,是刚从临时停车的小站上来的。此刻,它仿佛睡着了,柄收找的红油纸伞,古老、年轻、神采突突,与人类不相干的样子。
从其身上飘来一股草叶、露珠和泥土的清爽段神秘而天绝的农业气息……顿时,肺里像掉进了一丸薄荷,连荷般迅速溶化弥漫开来......
它小小的体温抚摸了我,将我湮没。
是什么样的诱惑,使之如此安然地伏在这儿,在冰凉的铁窗沟槽里?
它是一族光焰,一颗童话里的糖,一粒诗歌记忆中失踪的字母......和我烂熟的现实生活无关。
驮背七盏星子。不多不少,一共七盏。为什么是“七”?这本身就是一件极神秘的事。幼小往往与神性、博大有关。
我肃然起敬,不忍心去惊扰它。它有尊严,任何生命都有尊严。
它更值得羡慕——
像一个小小的纯净的世界,花园一样甜,菜畦一样清洁,少女一样安静,儿童一样聪慧和富有美德......
它能飞期,乘着风,乘着自己的生命飞来飞去。而人只能乘坐工具一且“越来越变成自己工具的工具了”(梭罗)。它不求助什么,更不勒索和欺压自己的同胞,仅凭天赋及本色生存,这是与人之最大区别。

它自由,因为不背负任何包被,生命乃其唯一行李。它快乐,因为没有复杂心计,对事物不含敌意和戒备。它的要求极其简单一有风和大自然就行。从躯体到灵魂,它比我们每个人都轻盈、优雅、健康而自足。
它一定来自某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那儿生长着朴素、单纯和亮的元素......
在心里,我向其鞠躬。我感激这只不知从哪儿来的精灵,它的降临,使这个炎燥的旅夜变得温润、清爽起来。
邻座顺着我的视线去搜素,啥也没发现,唉,不幸的好奇心。
长时间的激动,它终于让我累了。
闭上眼睛,我希望等自己醒来的时候——
它已像梦一样破窗飞走。
但我将记住那个梦,记住它振翅时那个欢愉的瞬间。

草芥
为了抽支烟,我来到列车最拥挤和最孤独的地方一两节车厢的衔连处。
扎堆在这里的,除了一脸冷漠,显示出自命不凡和矜持的烟民便是那些莲头垢面的外省民工了。
他们或躺或倚或蹲,不肯轻易站着,仿佛那是件很费气力的活儿。其神情、衣束、行李皆十分相近,让人猜想这曾是一支连队,一支刚从战场撤下,且全是伤病号的队伍。
他们一个个表情黯淡,呵欠连天,像是连夜赶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儿,而上路前又恰好干完很累的活……他们对车厢里的一切都没兴趣,一上来便急急地铺下报纸卷、麻袋片,急急地撂倒身子,仿佛眼下唯一要做的就是节省体力,仿佛有更累更重的活儿在前方等着......
他们是这世上最珍爱气力的人。气力是其命根子,就像牛马毛驴是农家老小的命根子,他们舍得喂,舍得给,却不舍得鞭抽,不舍得挥霍挪用。
突然涌上一股惶恐。我缩了缩绷紧的脖子,觉得这样悠闲且居高
临下地看对方“太不像话”——这显然不对!
总之,这隐含了某种“不对”。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要靠几个、几十个人来养活。而有的人,却要至少养活几个人……有人一上车就被引入包厢,领到鲜花茶几水果前。而有的人,却被苍蝇似的赶到这儿,且只准待在这儿。

他们不是苍蝇,是人!
我一阵胸闷,心里低低吼着。像有一团擦过坐便器的脏布堵在里面。
我并非厌恶自己,我只是想到了某些令我厌恶的人,所以才有要世界呕吐的感觉。
我相信没有谁饲养我,我靠自己养活。说不定我还养活了谁!
我在心里向他们致敬。我想蹲下去,蹲到和其一样的高度,恭恭敬敬让一支烟…但终于没做,怕人家误会。
他们不习惯白拿人家的东西。我遇到过这样的情景:长途汽车上,将几颗糖悄悄塞给邻座农妇的孩子,她害怕地往后躲,后来母亲发现了,竟掴了孩子一巴掌,嘴里骂:“叫你馋,叫你拿人家的东西……”
“人家”——一个多么客气又警觉的词。客气得叫人压抑,让人难受。
他们在睡觉。集体在睡觉。他们的梦仿佛是同一个,连脸上的表情都那么一致,不时地张嘴,不时地皱眉,不时地淌下一丝涎水,仿佛要把更多的空气吞下去,仿佛嫌鼻孔不够大......
只有空气无偿地支援他们,满足他们。
他们在打鼾。就像在自家炕头老婆身边那样打鼾。偶尔翻一下身喉咙里发出叽里咕噜,石块滚下山坡的响声……手趁机在行李上抓把,判断对方还在不在。
他们的神情像是在森林里迷了路。有时突然睁开眼,警觉地瞅瞅四周,然后用焦急、粘连不清的方言问头顶上的烟圈:几…几点啦?
他们似乎连句流利的话都说不出,又似乎还急着想说啥,却一时给忘了。
你索性将时刻和一路上的大小站全报给了对方。
他们满意了,眼里噙着感激,连连点头,倒身又睡了。
自始至终,你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
省的全都省下来了

——1996年
END
作者介绍
王开岭,男,1969年出生,山东滕州人。现居北京。作家、媒体人。历任央视《社会记录》《24小时》《看见》等栏目的指导和主编。
著有散文和思想随笔集《精神明亮的人》《古典之殇》《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激动的舌头》《王开岭作品·中学生典藏版》等十余本书,作品入录国内外数百种优秀作品选。
其作品因“清洁的思想、诗性的文字、纯美的灵魂”而在大中学校园拥有广泛影响,入录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新语文课本》和各类中高考语文试题,被誉为中国校园的“精神启蒙书”和“美文鉴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