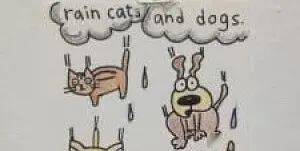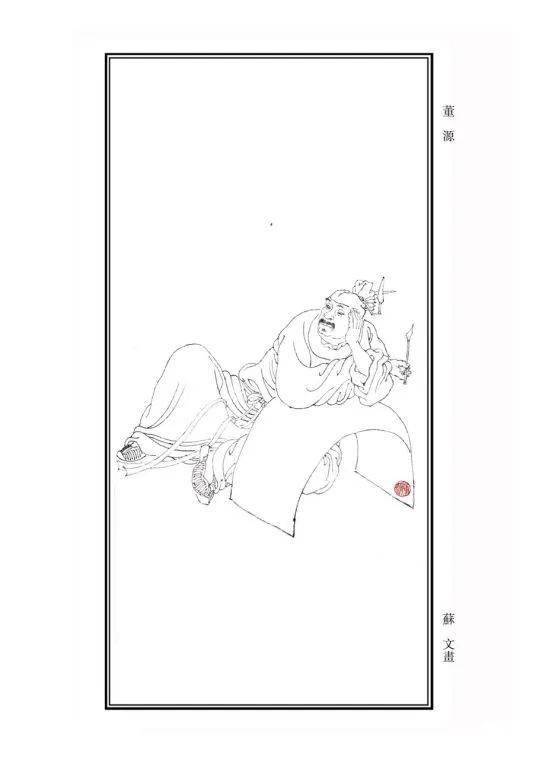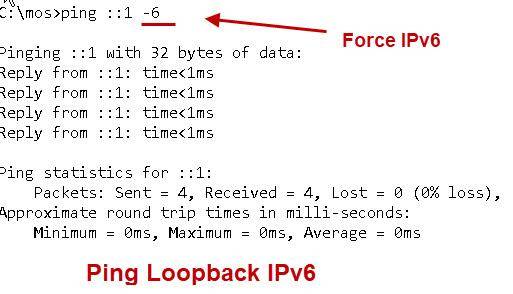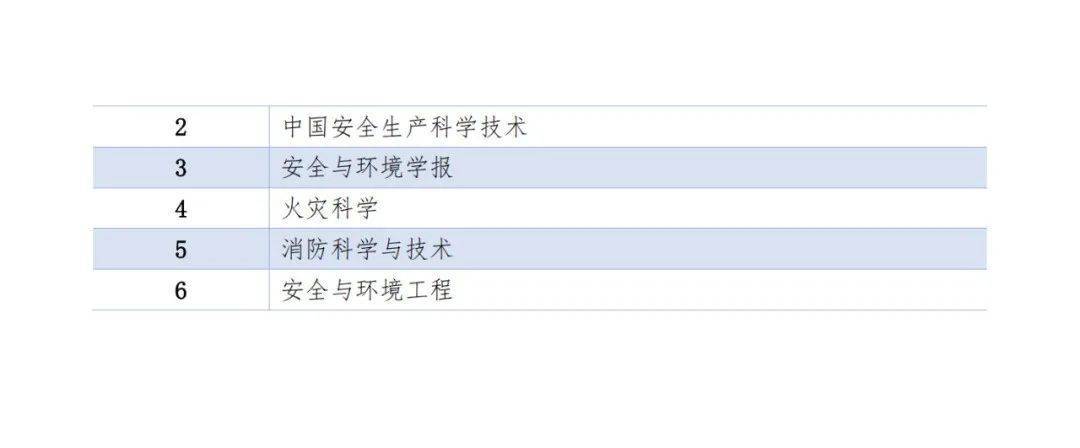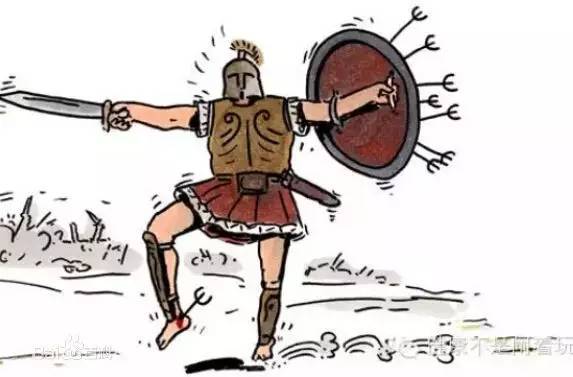
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原指阿喀琉斯的脚跟,因是其唯一一个没有浸泡到神水的地方,是他唯一的弱点。后人常用“阿喀琉斯之踵”比喻,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他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肋。
《荷马史诗》:英雄阿喀琉斯是凡人珀琉斯和美貌仙女忒提斯的儿子。传说他的母亲为了让儿子炼成“金钟罩”,在他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使其能刀枪不入。但遗憾的是,因冥河水流湍急,母亲捏着他的脚后跟不敢松手,被捏住的脚后跟不慎露在水外,所以脚踵是最脆弱的地方,全身留下了惟一一处“死穴”,因此埋下祸根。长大后,阿喀琉斯作战英勇无比,但却被帕里斯一箭射在脚后跟而身亡。
1. 抗体药的阿喀琉斯之踵

自从人类发现免疫动物的抗血清可以用来对抗感染,抗体就登上了疾病治疗的舞台。最早的单抗治疗采用纯化的鼠源单抗,毫无疑问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将其视为异物,产生抗药抗体。对鼠源单抗产生免疫应答的认知,导致了工程抗体的发展。从人鼠嵌合抗体、人源化抗体,到后来的全人源抗体,抗体工程手段将单抗中的非人序列降到最低的可能性。根据经典的免疫学理论,免疫系统可以区别“自我”和“非我”的蛋白质序列。全人源抗体中没有非人的氨基酸序列,因此人体对其产生抗抗体的可能性应该极低。2002年,第一个全人源单抗阿达木被批准上市。然而,大规模的使用彻底证明,全人源抗体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接近一半的患者在一段时间后产生了抗药抗体,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药效下降。抗药抗体的产生成为很多单抗药物临床使用的阿喀琉斯之踵。
2.经不起推敲的经典理论

免疫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机体免受外来入侵,同时不对机体本身的成分产生过度反应。经典的免疫学理论将其阐述为简单的“自我-非我”的二分法。抗原呈递细胞收集身体内的物质,将其分离成肽并呈递给T细胞。后者使用T细胞受体(TCR)扫描所提供的肽混合物,根据信号是否异源,决定是否触发免疫反应。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抗原呈递细胞同时携带着上千个“自我”抗原,其中可能仅混杂个别“非我”抗原,那么T细胞如何进行区分?上个世纪经典的免疫学理论告诉我们,这一步是通过胸腺对T细胞的“阴性选择”实现的,胸腺剔除与自身抗原反应的TCR,避免T细胞针对自身成分。每个幸存的T细胞上只表达一种TCR,像“锁与钥匙”一样识别“非我”抗原,激活免疫应答。
这套理论实际上非常经不起推敲。首先,免疫系统可以对自身与疾病相关的抗原(如肿瘤)反应,而通常忽视体内的许多无害的非自身蛋白质组抗原。其次,据估计自然界中的抗原肽至少在10的13次方,而体内的TCR库只有10的7次方量级,想要有效的保护宿主,需要构建一个比宿主生物大得多的免疫系统。另外,经典的“自我-非我”的免疫学理论,最大的问题是与进化论相违背:如果免疫反应是以内在序列差异为基础的,那么病原体将迅速模拟人体蛋白质组,从而永久躲避免疫系统。
3.生命的本质是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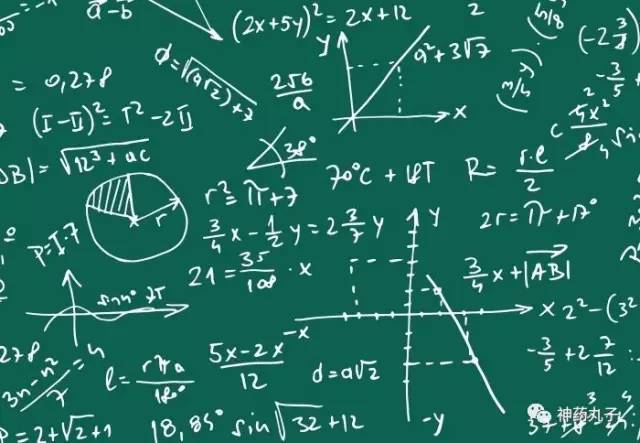
由于生物学研究手段的限制,对免疫系统如何区分在自我-非我一直是未解之谜。本世纪初,数学家掺和了进来,基于现有的实验科学发现,结合概率论为基础的数学分析,提出了全新的模型。免疫系统甄别体内潜在的异常和感染,在数学上可以被描述为将特定信号与嘈杂背景区分的任务。免疫系统持续的扫描机体内的所有抗原,机体通过一整套算法,在各个环节不断的提高信噪比,从而将可能有害的抗原识别出来。
这套计算模型的一些基础假设和所得的结论与经典的免疫学十分不同。首先,“自我-非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误导性的,因为识别的直接原则不是根据宿主的固有蛋白质组,而是根据抗原的统计识别的变异量。“危险”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是非”问题,只要超过其关键的特征水平,每个自身抗原也都可能被认为是“危险的自我”。TCR对抗原的识别不具有特异性,不存在“钥匙与锁”的关系,T细胞具有强大的调节抗原敏感性和应答阈值的能力。免疫系统的很多环节,包括胸腺阴性选择、抗原呈递细胞的呈递等,本质上起到的是“过滤器”的功能,目的是提高信噪比。
这些模型基于的一些重要的假设,不能被明确的实验科学证实。同时,这些模型也似乎没太受到生物学家的重视(引用量不大,可能是和我一样看不懂公式)。然而,这套思维可能在更大的维度上,揭示了生命的本质,而非局限于具体的结构和功能。在人工智能发展之初,一些生物学家也开始从计算的视角来思考生命的问题。美国科学家阿德勒曼在阅读沃森的《基因的分子生物学》时意识到,DNA聚合酶合成互补的DNA的机制与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在1936年描述的图灵机几乎完全一样。1994年,阿德勒曼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DNA计算机理论,认为生命系统可以解释为一台基于分子算法的多层次的计算网络。生长、发育、分化、免疫反应表面上看是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在时间空间上的精巧匹配,但本质上是对基因组中包含的信息和程序执行的表现。
4.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随着结构生物学等的发展,对免疫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认知在过去几年中取得巨大进展。TCR对抗原的识别既具有高度特异又高度交叉,这就推翻了之前TCR对抗原的识别不具特异性的假设。日益增长的TCR的结构数据库不仅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免疫学概念,也形成了一些可测试的假设。目前,已经有不同的计算模型可以预测生物药在人体中产生抗药抗体的可能性。然而,这次科学似乎依然没有很接近真理。诺和诺德的长效重组FactorVII在临床III期有11%的病人产生了抗药抗体,并且面临凝血障碍的生命威胁。辉瑞的PCSK9单抗由于抗药抗体产生使疗效下降,在临床III期被终止。这些似乎昭示着一个残酷现实,基于目前认知的人工的算法比起人体的生物算法,还是弱爆了的。
哲学家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中说,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并不是真理不断的战胜谬论,而是通过不断的猜想和反驳而不断达成的认知升级。爱因斯坦与波普尔都认为科学理论是人类的“创造物”而不是“发现”。 “真理”是一个宗教概念而不是科学概念。或者说,自然界背后并没有隐藏着“真理”等待我们发现,即使我们手中握着“真理”,也不可能知道它就是“真理”。波普尔的学生沃特金斯总结科学理论的三条准则:深刻、统一、预测。任何现象都可以有无数种解释,但只有可以用于预测的解释才是有用的理论。虽然在与免疫系统斗智斗勇的路上,目前的认知和理论在生物算法面前依然黯然失色,但是似乎已经有迹可循,而且越做越好。我们依然可以乐观的说,现在我们手中有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但将来还可能有更好的理论来代替它。
来源:神药丸子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