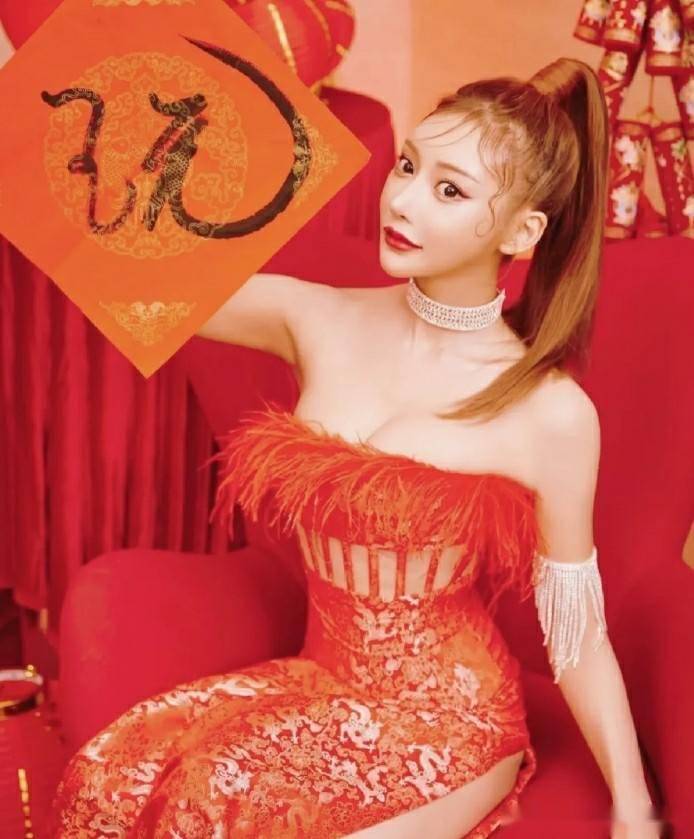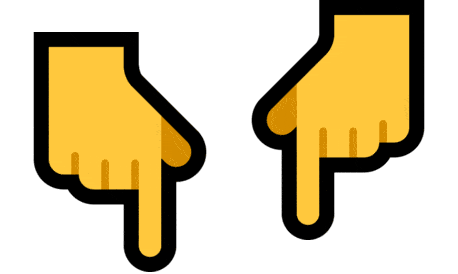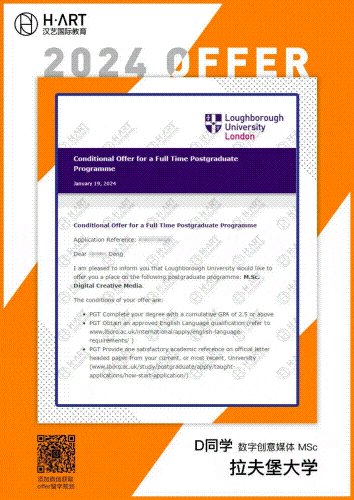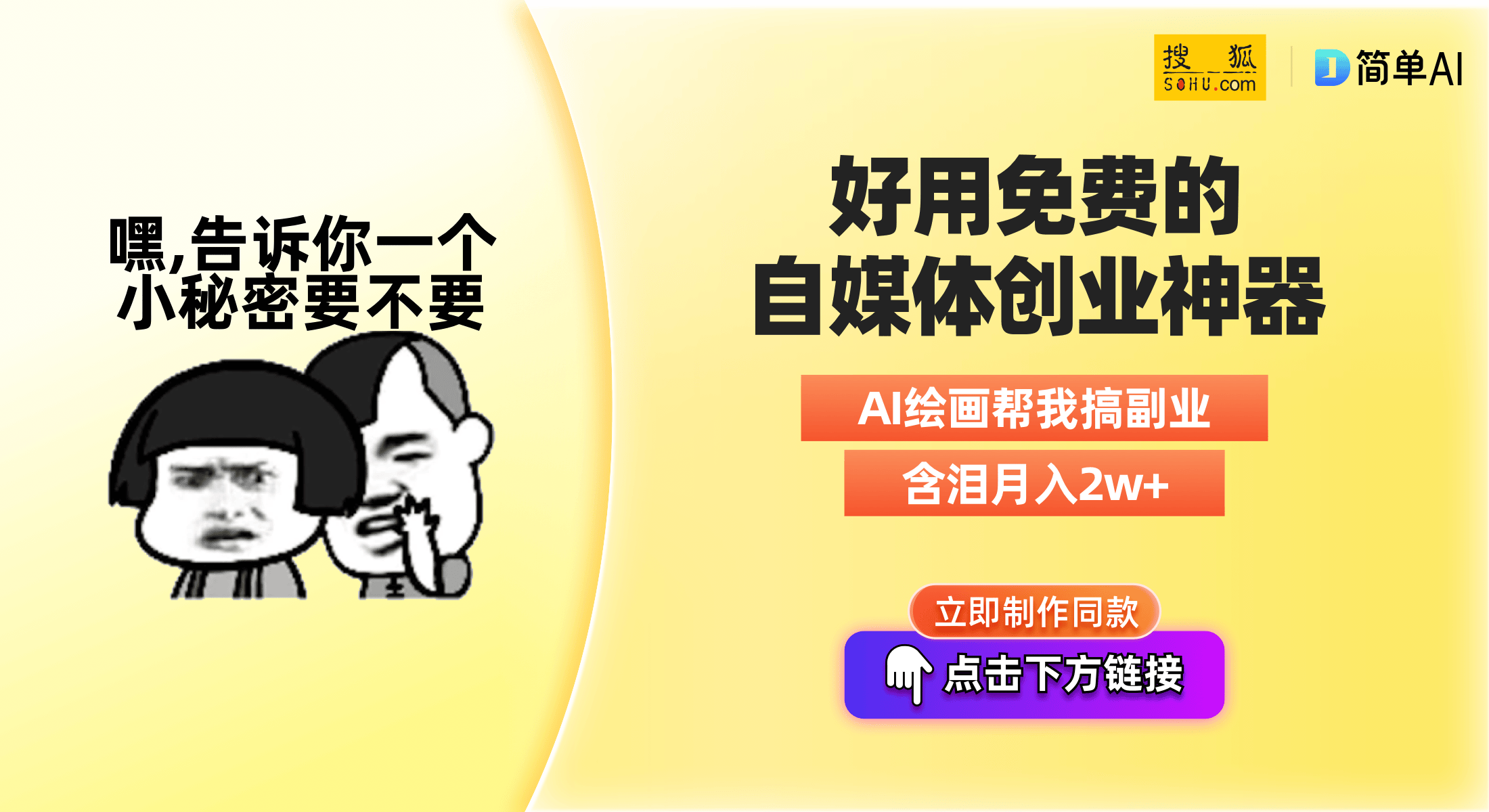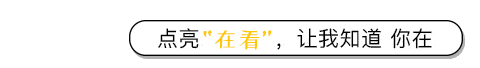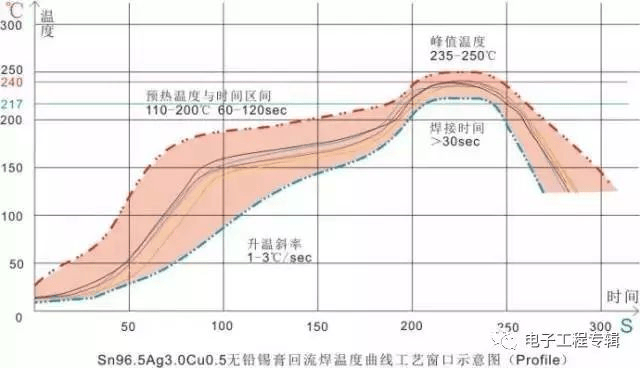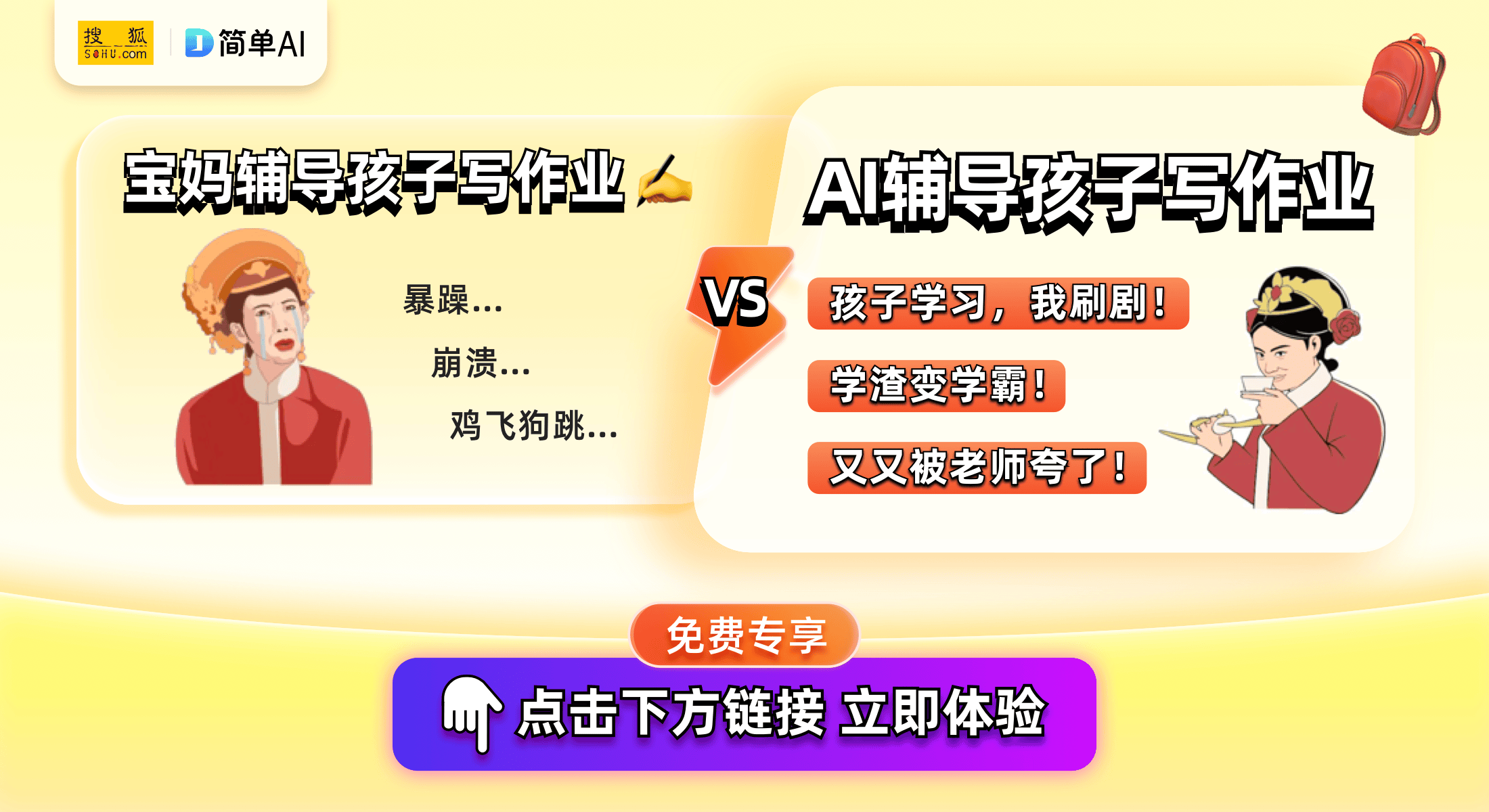卡尔维诺说:“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历久弥新,也因为它是千百年来时代的总结,常读常新。”为了更好地凸显丁玲纪念馆的文化属性,打造一座高质量的文学殿堂,我馆特别策划推出了《经典品读》栏目。此栏目将在每月推出一篇丁玲或其他国内外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供大家品读,以期在阅读中感受它的魅力,通过阅书,读己,充实读者的精神和生活。
这一期我们要推出的作品是作家霍达斯创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视频来源:哔哩哔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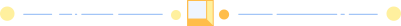

作者风采
霍达,女,回族,1945年11月26日出生于北京,作家、国家一级编剧。1966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任北京市园林局、市文物局翻译。曾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1976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不要忘记她》。
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6年至1987年,出版中篇小说集《红尘》以及报告文学《绿叶的荣誉》《渔家傲》《万家忧乐》《起步于黄帝陵前》《小巷匹夫》等。
1987年创作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该作于199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1997年,出版长篇小说《补天裂》,该作品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1999年8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05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搏浪天涯》。
2010年,创作话剧《海棠胡同》。
2015年,《补天裂》再版。
2020年1月,出版游记作品《听海》。
读者评价
冰心:看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
张丽君:《穆斯林的葬礼》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壁、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展现了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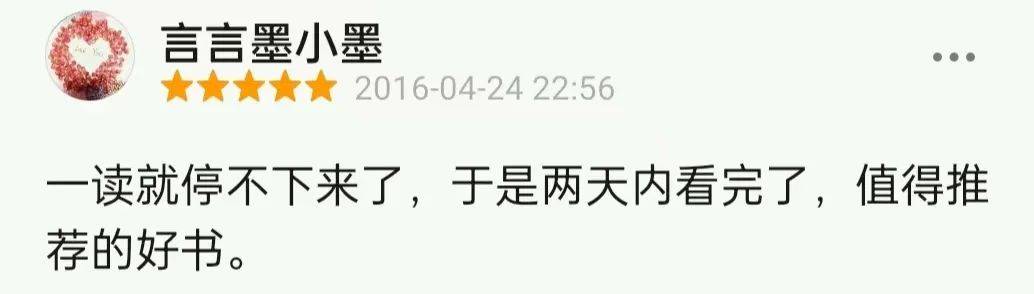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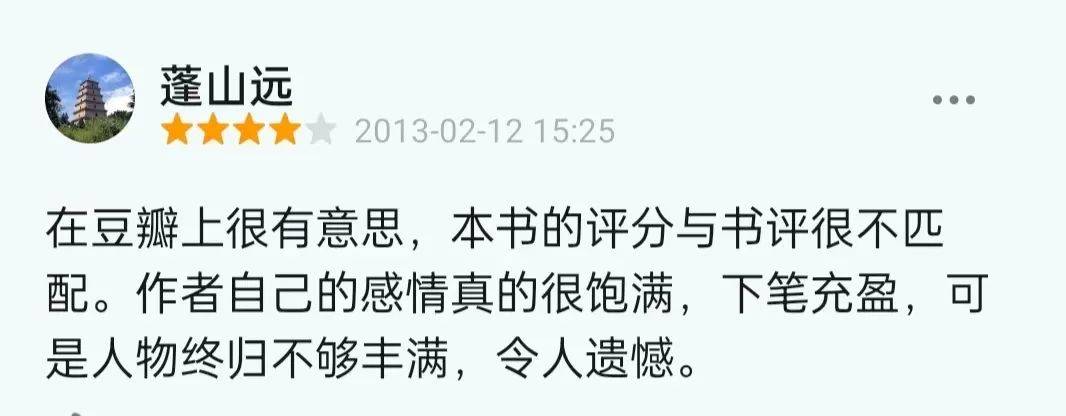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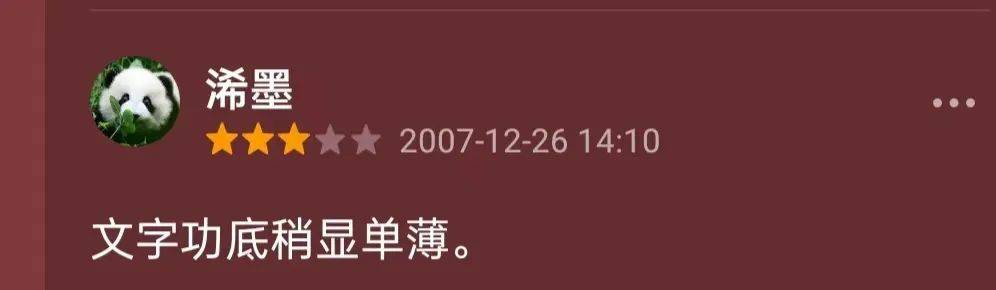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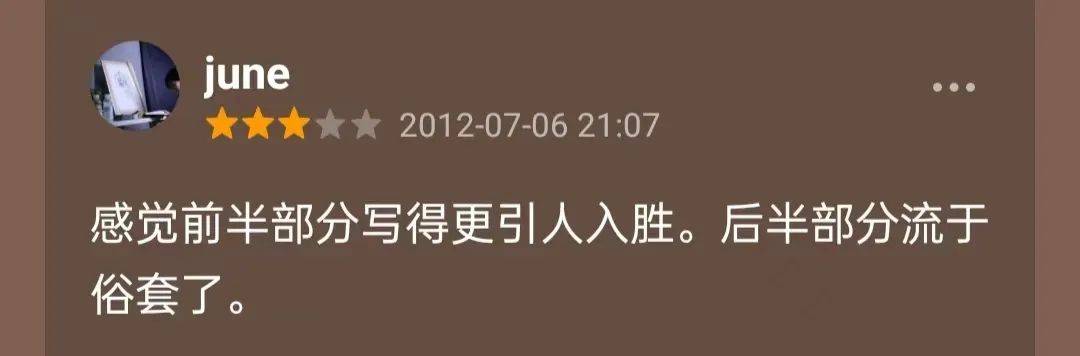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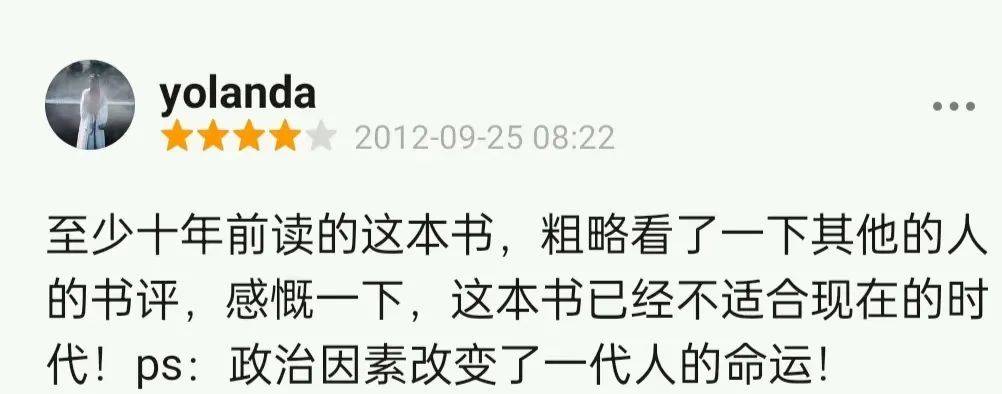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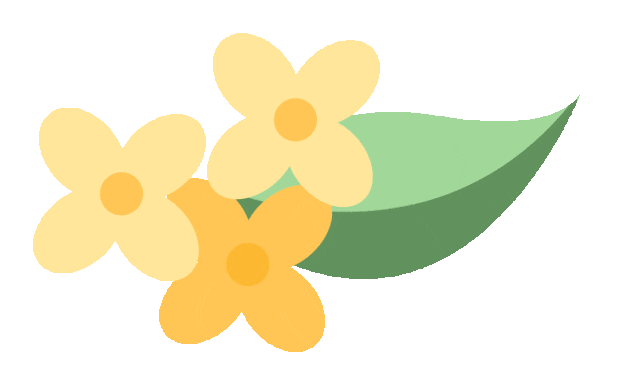
作品荐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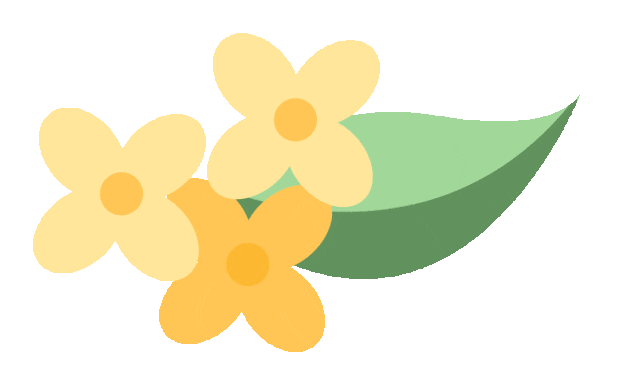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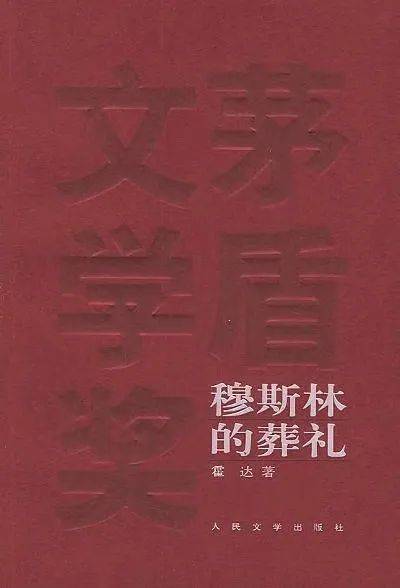
《穆斯林的葬礼》是霍达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原载《长篇小说》第16、17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初版。
该小说以回族手工匠人梁亦清的玉器作坊奇珍斋升沉起伏为主线,在历史的背景下描写梁家三代人不同的命运变迁,表现了主人公为追求理想和事业,为完善自身素质所发出的蓬勃不息的命运意识。
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1年12月,土耳其“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以线上形式举办了首场读者沙龙,在线阅读分享了土耳其语版《穆斯林的葬礼》。
霍达说:我在稿纸前与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久远的跋涉。每天从早到晚,夜以继日,常常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心都在小说中。当我一个个把他们送离人间的时候,我被生离死别折磨的痛彻肺腑……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虽然读者对此书评价标准不一,有人认为作者文笔不行,没有写出一个民族恢弘的变迁史;有人觉得韩子奇和梁冰玉的婚恋观不正;有人却沉迷此书无法自拔。我就是其中之一,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内心久久不能平复。小说中的情节,故事中的人物,活生生的浮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个家族,六十年的兴衰沉浮,几代人的情感纠葛,有执着的追求,有真挚的爱情,有世俗的烦恼,有宗教的信仰,有战争的苦难,有时代的变迁……最终尘埃落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这人生又有谁能真正把握的住?真可谓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读一读《穆斯林的葬礼》的葬礼,你会从中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
原文欣赏
穆斯林的葬礼(节选)
霍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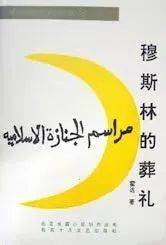
天黑下来了,“伏天儿”还在悠然地鸣唱,但白天的炎热已经消退了,微风吹来,让人感到一丝凉意。夏夜的晴空,撒满了无数的星斗,闪烁着清冷的光芒。西南天际,一道弯弯的新月,浮在远处的树稍上空,浮在黑黝黝的房舍上空,它是那么细小、玲珑,像衬在黑丝绒上的一枚象牙,像沉落水中仅仅露出边缘的一只白璧,像漂在水面上的一条小船,这小船驶向何方?
新月在姑妈的房里坐了很久才回去睡觉。父母的争吵,高考志愿的悬而未决,都使她不安,而又无处诉说,只有姑妈最疼她,最宠她,最能安慰她,遇到不愉快的事儿,她总是首先在姑妈那儿寻求安慰,姑妈就把话正着说,反着说,掰开揉碎地说,直到把她哄笑了,娘儿俩才算完。但是这一次,姑妈的法宝失灵了,报考大学这件事儿太大了,超过了姑妈的权限,她可做不了主,只是反复说:甭着急,再跟你妈商量商量;甭着急,你妈疼你,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什么事儿还不都尽着你?她是不放心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再跟她好好儿说说!姑妈甚至还说:我寻思着,一个姑娘家,上不上大学也不当紧……唉,姑妈不识字,她懂得太少了,话说得啰里啰唆,糊里糊涂,不得要领,她安慰不了新月。
新月从姑妈那儿出来,忐忑不安地走回西厢房去。她抬头看到天上的那一弯新月,便想到了自己,她和那个神秘的天体是一样的名字。十七年前,也是新月升起的时候,她在人间落生了,像弯弯的新月一样升起来了,十七年,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以后的路怎么走呢?天上的月亮有自己的运行轨道,从容不迫地向前走去,她呢?她现在却在一个十字路口,茫然徘徊。
她站在天井里,望望上房。上房东间里父母的卧室,窗纸上已经没有灯光,不知他们睡了没有。她想再去跟父母谈谈,但走到廊下,听听里面没有声息,便又犹豫地站住了。也许他们已经睡着了,她不敢叫醒妈妈。站了一会儿,就悄悄地退去了。
回到西厢房,她没有开灯,便浑身无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屋里很暗,朦胧的月光从窗外反射过来,窗纸是一片淡淡的灰白色,墙边的立柜、梳妆台、写字台都只是幢幢黑影,她像走进一个无人的空谷,感到孤独和凄凉。她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张两头装着镂花栏杆的双人大铜床,是她从小睡的地方,也是妈妈睡过的地方。姑妈说,妈妈生哥哥的时候和生她的时候,都是住在这儿的。岁月太久了,她已经记不起自己在婴儿时期是怎样被妈妈抱在怀中喂奶,母女之间是怎样亲密无间。在她的记忆中,幼时陪着她睡觉,帮她穿衣服,喂她吃饭,带着她在院子里玩儿……这一切都是由姑妈来做的。她上小学了,姑妈给她缝了书包,送她到学校门口;放学时,姑妈在学校门口等她,唯恐她走迷了那一段长长的路,也怕街上的男孩儿欺负她。这样一直延续了好几年,直到她上了初中,姑妈确信她已经有了自卫能力,才停止了迎送。但每当放学的时候,总是眼巴巴地等着她回家,如果她回来晚了,姑妈一定焦急地在大门外瞭望。记得十二岁那一年,她第一次因为床单上的血痕而惊慌失措,掩饰不及而遭到了妈妈的白眼:“这么大的丫头了,连这都不懂……”是姑妈赶忙拿去洗,还悄悄地对她说:“新月,你是大姑娘了,别怕,这不是病,也不是伤,姑妈告诉你……”从那时起,已经五年了,她觉得自己真的一天天长大了,渐渐地会料理自己的一切,姑妈为了让她清静,就不再陪她睡,搬到倒座南房里去了,可是仍然主动地为她缝补浆洗,默默地关心着她的一切,一直到今天的生日晚餐……而这些,似乎妈妈都不大在意。现在,她高中毕业了,面临着激烈争夺的高考,这是她人生中的一大关头,不但需要自己去全力拼搏,也多么需要亲人的支持和鼓励啊!爸爸显然是支持她的,但是爸爸似乎又顾虑重重,没有妈妈的点头,爸爸是很难做出最后决定的,他今天的话越说越无力,还是要看妈妈的脸色。妈妈嘴里说“不管”,而实际上却是坚决要管,要阻拦,要在这决定命运的一步改变女儿的道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她烦乱地从床上坐起来,打开了台灯。台灯下赫然摆着她的报名单,“升学志愿”那一栏还空着,她不知道明天将怎样交给老师?已经立下破釜沉舟之志的姑娘面前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这障碍竟然来自她的生身之母!
泪水洒在那张还没有填写志愿的报名单上。她掏出手绢儿,轻轻拭去泪痕,珍惜地把那张纸夹在英语课本里,两肘支在书桌上,对着一盏孤灯,思绪茫然。她的目光落在台灯旁边的那只小巧的硬木雕花镜框上,那里面,镶着一张发黄了的六英寸照片,是她和妈妈的合影。照片上,妈妈文静、端庄,脸上浮现着温柔、慈爱的笑容,纤细优美的手,一只揽着她的腰,一只拉着她的手;她坐在妈妈的膝上,甜甜地偎依着妈妈,两只不谙世事的大眼睛望着镜头微笑,充满了甜蜜。她那时留着长发,垂到肩上,穿着白色的纱裙,白色的长袜,白色的小皮鞋,就像是妈妈抱着一个玩具小洋娃娃。那时候,她才两岁吧?可是,她的脸型、眉毛、眼睛、鼻子、嘴巴都已经看得出很像妈妈。现在,她长大了,她从镜子里看自己的时候,觉得越长越像妈妈了。但是,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和她合拍过照片,十七年,只留下这么一张。她无限依恋地望着这张照片,真希望自己重新变小,再退回到妈妈的怀抱中去,体味那越来越淡的母女之情。照片上的妈妈比现在年轻得多了,那时妈妈还是一个美丽的少妇,烫着鬈发,穿着旗袍。现在妈妈老了,装束也改换了,但脸型、眉目并没有多大变化;变化最大的不是形象,是妈妈对她的情感!她好像又看见了妈妈的那阴晴难以捉摸的脸,虽然也有过笑容,也有过亲切的话语,但更多的是冷漠,有时甚至是冷若冰霜,使她常常本能地惧怕妈妈,回避妈妈。她多么希望妈妈不要变,永远像照片上那样和蔼可亲!往日的温柔慈爱到哪里去了呢?是什么力量在母女之间造成了一道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时时可以感觉得到的鸿沟?妈妈,您怎么让女儿无法理解啊?
往期推荐
经典品读|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经典品读|钱钟书:围城
经典品读|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
经典品读|余华·活着
经典品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END
编 辑 | 王思戈
初 审 | 郑美林
复 审 | 张 兰
终 审 | 毛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