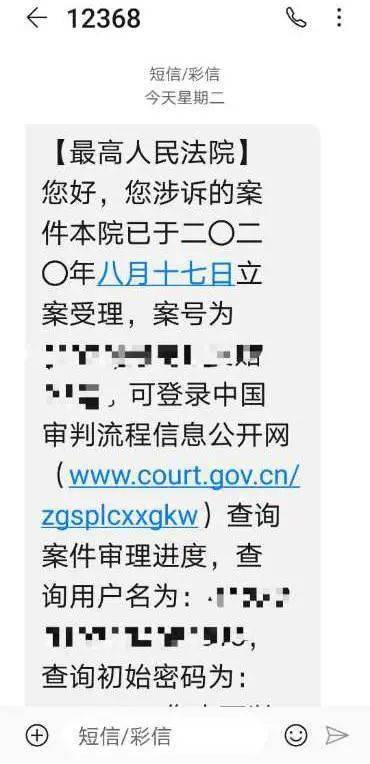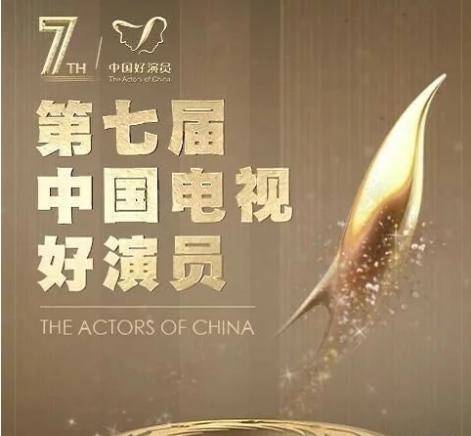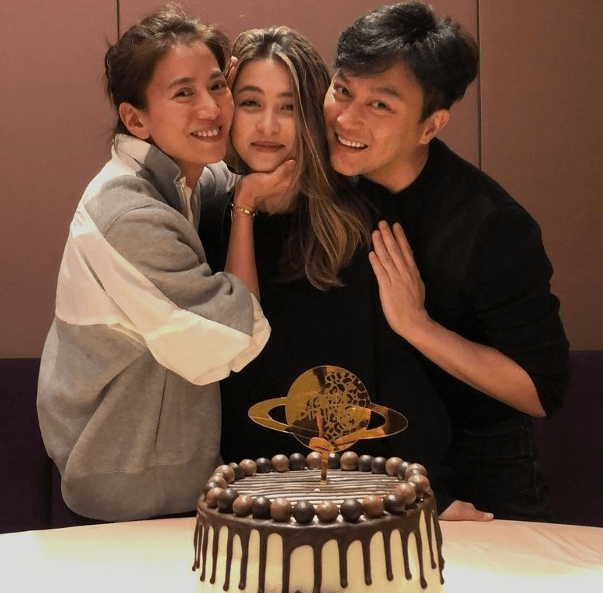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民义》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首诗便是这首《母亲的专列》,当时听着郑西坡朗读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留下了眼泪,或许是在外漂泊了多年,远离父母太久,突然听到这首诗,内心的情感崩塌了,就差两天就到了今年的母亲节,我依然没有办法回家陪母亲,这么多年,那些留在母亲身上的病痛从来不曾因为我的远离而减弱,一想到心里觉得格外的伤感。
《母亲的专列》
这是您惟一的一次乘车
母亲您躺在车肚子里
像一根火柴那样安详
一生走在地上的母亲
一生背着岁月挪动的母亲
第一次乘车旅行
第一次享受软卧
平静地躺着像一根火柴
只不过火柴头黑
您的头白
这是您的第一次远行啊
就像没出过远门的粮食
往常去磨房变成面粉时
才能乘上您拉动的
那辆老平车专列
我和姐姐弟弟妹妹
陪伴着您
窗外的风景一一闪过
母亲您怎么不抬头看看
只像一根躺着的火柴
终点站到了
车外是高高的烟囱
《母亲的专列》
这是您惟一的一次乘车
母亲您躺在车肚子里
像一根火柴那样安详
一生走在地上的母亲
一生背着岁月挪动的母亲
第一次乘车旅行
第一次享受软卧
平静地躺着像一根火柴
只不过火柴头黑
您的头白
这是您的第一次远行啊
就像没出过远门的粮食
往常去磨房变成面粉时
才能乘上您拉动的
那辆老平车专列
我和姐姐弟弟妹妹
陪伴着您
窗外的风景一一闪过
母亲您怎么不抬头看看
只像一根躺着的火柴
终点站到了
车外是高高的烟囱
小时候我们怀揣梦想,任性地追逐诗和远方,而忽视了妈妈在背后为你准备的行囊。长大后我们力求瞩目,想要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却忘记了你在妈妈心中永远是她的焦点。成人后被忙碌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就把忙作为疏离母亲的借口,而妈妈们都信以为真,渐渐地我们习惯了妈妈的付出,而忽略了岁月在母亲身上所停留的痕迹。

想起了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正是青春期,和母亲经常斗嘴。终于有一天,男孩一气之下,甩门而去,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这时有个老人来了说:“孩子,你怎么不回家啊。”男孩便说起了母亲的不是,说母亲不爱他。老人微笑着听完后说:“孩子,你不妨到家看看你母亲在做什么”男孩似乎听到老人叹了口气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当男孩回到家后见到母亲坐在家门口看书,可哪是在看书,分明是在看着门口。看到男孩回来后母亲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眼中还闪着晶莹的泪花,但母亲只是淡淡的说了声:“你回来啦。”就准备转身回屋,低着头尽量不看男孩,可是男孩看得分明。母亲在转身的一刹那,泪花滴落了下来。男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哭着抱住母亲说:“我错了,对不起,妈”母亲只是说了声“没事,吃饭吧”从那刻起,男孩懂了,原来最疼自己的是母亲,原来不会放弃自己的还是母亲,原来无论你做错了什么母亲都会原谅你。

每次看到小朋友和妈妈斗嘴,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心中一直想着幸好我没有和母亲斗嘴,幸好母亲还在身边,去年回家的时候,偶在母亲头上发现白发了,当我惊讶的叫出:“妈妈,您头上有白头发了。”母亲您也只是微微笑了一下,竟连一声抱怨累的话语也没有。
母亲,您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却有着不同内涵的事务。不是吗?我一天天地长大,懂的体贴您了,而您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呵护我。老子曾训言:“上若善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如果说有道德的人像水,那么,母亲就是水,母亲心地清澈如水,本性柔和如水,虚怀沉默如水。
又想起了郑西坡的那首《母亲的专列》,在诗人的笔下,他的母亲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坐过火车,一生唯一的一次乘车,也是最后一次乘车,却是在去往火葬场的路上,灵车变成了诗人母亲的“专列”。诗人母亲的一生,像一根火柴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子女最初的路,当她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光芒,她亦如一根燃尽的火柴那样安详宁静。
如此,我只想说,趁母亲还在的时候,多回家看看,多和母亲打打电话,多和母亲聊聊现在过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多跟母亲说一句:妈妈,我爱你。